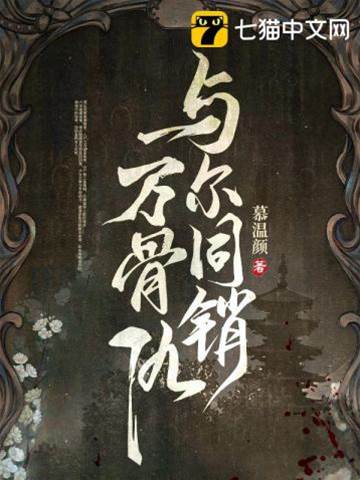《攻玉》 第38章 (2)
嚴司直奇道:“既然懷疑那人是騙子,你們主家為何不報?”
“主家早就報了,還托人去問縣里的法曹,說那道士是的,行騙卻在長安,這事到底歸長安萬年縣管,還是歸管?可沒等主家問明白,后苑就蹦出大妖,隨即整棟樓都被封了,這事也就擱置下來了。”
藺承佑沉不語,從小佛堂里的格局來看,那道士不像騙子,縱算匠作施工時不小心砸穿了地面,憑此人的功底過來做些補救并不難,為何連面都不了?
正因為逍遙散人沒再面,也就沒人發現底下的陣眼被砸穿了。匠人們闖了禍不敢告訴賀明生,賀明生不懂道法看不出端倪,所以直到二怪都跑出來了,彩樓還夜夜笙歌。
小佛堂……小佛堂……藺承佑在心里盤算,人人都對這座森的小佛堂避而遠之,有人卻利用這一點在里頭施展邪。
他的思緒凝結在小佛堂里香案下發現的那枚七芒引路印上。
七芒引路印邪門至極,只有晚間才能行事,作法時需全程無人打擾,小佛堂算是最好的場所。
兇手不想讓人窺見自己的所作所為,不得人人都不敢去小佛堂……而為了萬無一失,一個“森”可不夠,論理還應該做點別的。
藺承佑心中一:“萼大娘可曾聽誰說起自己在小佛堂里撞過鬼?”
萼姬張地點頭:“有有有,幾月前就人說過此事,后來接二連三有人撞鬼,奴家好像……好像也見過的。”
嚴司直古怪道:“見過就是見過,沒見過就是沒見過,什麼‘好像見過’?”
萼姬一甩帕子:“因為奴家也鬧不清那東西是人是鬼嘛。”
藺承佑興趣濃厚地問:“你見到的那東西長什麼模樣?”
Advertisement
萼姬畏懼地吞了口唾沫,那件事都過去好些日子了,想起來還是覺得發怵。
“大約兩個月前,記得那日是十五,有幾位外地來赴考的冠子弟來樓里喝酒斗詩,點名要聽曲。奴家看他們模樣還算斯文,就了卷兒梨和抱珠去伺候,說好了只奉曲詩行酒令,不伺候別的。郎君們也都答應了,哪知喝到半夜,席間有位郎君強抱著卷兒梨求歡,抱珠拽不開那人,眼看要壞事,只好跑出來找奴家。
“等奴家趕過去時,卷兒梨裳都被撕壞了,那狗東西喝得爛醉,脾氣也大,被我們拉開時還憤憤了卷兒梨幾個掌,卷兒梨一皮得像清水做的,臉當時就腫了起來。
“奴家氣得牙都要咬碎了,連哄帶攆把這幾個狗東西趕出去了,好不容易,再回頭就找不到卷兒梨了,奴家知道這孩子面上不說話,心思重得很,了這樣一份委屈,心里指不定多難呢,忙和抱珠去尋,哪知卷兒梨不在房里,只好又去園子里找。
“園子大,又是深夜,奴家想起后苑有口井,唯恐卷兒梨尋短見,也顧不上鬼不鬼的了,一進去就跟抱珠分頭去找。園子里一個人都沒有,越往里走越僻靜,走到小佛堂附近的時候,奴家忽然看見一個影子從里頭躥出來——”
萼姬說到這的時候,聲音猛地一抖。
“奴家看見、奴家看見一只紅裳的鬼。”
“紅裳的鬼——”嚴司直起了疑,“天那麼晚,你離得很近麼?為何連裳都能看清。”
萼姬呆了一呆,仿佛不知如何接話。
藺承佑邊出一抹嘲諷的笑意:“萼大娘方才不是說了麼,那晚是十五。”
Advertisement
萼姬忙不迭點頭:“對對對,那晚月頭大,地上像撒了一層銀霜似的,奴家忘了帶燈籠出來,但也覺得四下里亮的。”
“看清鬼的模樣沒?”
萼姬頭搖得像撥浪鼓:“奴家沒敢盯著看,那鬼又跑得快,只覺得眼前紅影一閃,鬼影一霎兒就不見了。”
藺承佑:“沒看清模樣,總該對高矮胖瘦有些印象,覺得眼還是眼生?”
萼姬尋思一陣,很篤定地說:“如果是人,奴家早該認出來了,況且奴家活了這些年,從沒見過誰可以飛那麼快,那東西不可能是人,只能是鬼。”
“裳、簪環、香氣……就沒有一點悉之?”
萼姬苦著臉:“不過是一閃神的工夫,奴家事后也不敢追想,就知道那東西穿著襦,別的奴家早就忘了。”
藺承佑一不看著萼姬,萼姬頂住藺承佑的視線,不知熬了多久,就在不安地挪腳步時,藺承佑漂亮的嗓音響起:“故事還沒講完吧,抱珠找到卷兒梨沒?”
萼姬慶幸道:“找到了,奴家嚇得屁滾尿流,扭就往回跑,迎面就看見一群人找來,原來抱珠在綠蝶亭找到卷兒梨了,這孩子躲在亭子里哭呢,兩人過來尋我,半路到沃姬和魏紫們,幾人便結伴同行,們看我魂不守舍,忙問出了何事,奴家看卷兒梨臉上傷得不輕,只說撞鬼了,也沒敢逗留,當即帶們回屋藥膏去了。”
屋子里沉默下來,藺承佑食指一下一下敲擊著桌面,約聽見樓下衙役和人們說話,伴隨著略顯焦躁的腳步聲。
未幾,他開口道:“小佛堂是用來鎮鬼的,起初也的確靈驗了一陣,如果連小佛堂都開始鬧鬼,樓里的人必定驚訝萬分,第一個說自己在小佛堂撞鬼的人是誰?萼大娘總該有些印象。”
Advertisement
萼姬了把額頭上的汗:“在小佛堂附近撞鬼的不止奴家一個,奴家聽過就算,實在鬧不清第一個撞見的人是誰。”
一邊說一邊忐忑地打量藺承佑,本以為又會被刁難,哪知藺承佑主替圓場:“傳言麼,聽到時已經半真半假,想找出源頭哪有這麼容易,萼大娘想不起來也不奇怪。”
萼姬出個比哭還難看的笑容:“世子真是明白人,奴家盼著世子早日抓住兇手,恨不得把知道的都告訴世子。”
藺承佑真切地看著萼姬:“萼大娘的真誠,我已經覺到了。今日就先問到這吧,萼大娘出去的時候告訴衙役,賀老板上來回話。”
萼姬如釋重負,剛退到門口,就聽藺承佑道:“忘告訴萼大娘了,那晚你看到的‘鬼’很有可能就是兇手,如果你回房后想起什麼,馬上讓衙役給我傳話。”
“兇手?”萼姬駭然回頭,“那不是一只鬼嗎?”
藺承佑壞笑了下,并沒有答話的意思,萼姬盯著藺承佑看了一陣,心神不定地點點頭:“奴家回屋后一定好好想想。”
萼姬走后,嚴司直一邊書寫一邊道:“承佑,不覺得這個萼姬說話百出嗎?前面說‘奴家也鬧不清那東西是人是鬼’,后面改口‘人不可能飛那麼快,絕對是只鬼’。”
藺承佑諷笑道:“嚴大哥,你猜這話是在說給我們聽的,還是說給自己聽的?”
嚴司直擱下筆:“難道心里有什麼疑,想借著這話說服自己?”
藺承佑笑道:“我猜要麼想起那鬼像誰了,可心底又不愿相信,所以用這種法子說服自己。要麼——”
“自己就是兇手?”嚴司直接過話頭,“也是,都到這個當口了,除了兇手還有誰會撒謊?承佑,何不用瑟瑟珠試試這個萼姬,兇手會武功,究竟是不是,一試就知道了。”
Advertisement
藺承佑搖頭:“試不了了,這法子只能用一次,兇手知道我故意試探,愿被擊壞一只眼珠也不會餡的。”
嚴司直扼腕:“那就只能一個一個盤查了,可是我們連兇手與姚黃姐妹有什麼仇怨都不清楚,不清楚機如何往下查。”
“藏得再好也有餡的時候。”藺承佑垂眸看著桌上的證詞,“其實萼姬是兇手還好說,機也好,淵源也罷,總歸能查出來。但萬一沒撒謊呢,說到那鬼時屢次出疑的神,分明是想起了什麼。”
嚴司直思量道:“事關命安危,沒道理包庇兇手,何況萼姬是個極善保全自己的人,這當口還撒謊,我愿相信自己就是兇手。”
藺承佑想了想,對門外的衙役道:“讓賀老板再在樓下等一會,先把卷兒梨、魏紫和抱珠來問話。”
第一個來的是卷兒梨。
似乎有些神不濟,進屋后也不開腔,沖藺承佑和嚴司直行了一禮,便默默退到一旁。
嚴司直端詳著卷兒梨,心里暗覺可惜,這胡姬出奇的貌,可惜神態有些呆滯,人一呆,容貌就減了幾分。
藺承佑頭一次正眼打量卷兒梨,都說滕玉意跟卷兒梨葛巾有些像,可他沒看出哪兒像了。
非要比較的話,眼睛倒是有點神似,都是一樣的杏圓清澈,但滕玉意那雙眼睛里盛滿了水,長長的睫一眨,水就像是漾開來似的,一顰一笑都比卷兒梨的眼睛靈,只可惜水里盛的全是壞主意。
他在心里哼了一聲,拿起香囊問卷兒梨:“見沒見過這香囊?”
卷兒梨輕輕搖頭:“奴家昨夜是第一次見。”
問完卷兒梨,藺承佑又挨個把抱珠和魏紫進來。
不出所料,三個人都沒見過香囊。
至于兩個月前的十五發生了何事,抱珠和卷兒梨的說法與萼姬一致。魏紫那晚在前樓陪客,并不清楚卷兒梨曾遭人欺侮,但后來在園中的經歷,也與萼姬的敘述相吻合。
藺承佑接著問:夜間可曾見過誰在小佛堂附近出沒?第一次說自己在小佛堂撞鬼的又是誰?
三人都說沒見過,但都記得第一次提到自己在小佛堂撞鬼的,恰是萼大娘。
最后打聽越州人,卷兒梨等人均一無所知。眼看問不出什麼,藺承佑只好先放們回去。
嚴司直面復雜:“說來說去,第一個說自己在小佛堂見鬼的就是萼姬自己?倒是聰明,別的事上有所瞞,唯獨在卷兒梨的事上肯說實話,估計心里也清楚,這種事一問就知真假。”
藺承佑了下:“是不是實話,暫時還下不了定論。現在只能證明那晚卷兒梨四個曾結伴而行,萼姬卻是后面才跟們匯合,一個人獨的時候,究竟是撞鬼了還是去了小佛堂,目前可只有自己一個人的說辭。”
嚴司直困地“咦”了一聲:“承佑,今日你句句不離‘小佛堂’,是不是在里頭發現了什麼。”
藺承佑一拍腦門,轉過頭笑道:“忘告訴嚴大哥了,昨晚我兩個小師弟發現有人曾在小佛堂施邪,從布陣的路子來看,極有可能就是害死青芝的兇手。我懷疑有人故意四散播小佛堂鬧鬼的傳言,目的是為了讓人不敢靠近小佛堂。”
嚴司直怔住了:“照這麼說,萼姬豈不是嫌疑最大?這就奇怪了,香囊出自越州的桃枝繡坊,但萼姬卻是土生土長的長安人,何時去的越州,又為何要殺姚黃姐妹??”
藺承佑腦中冒出一個念頭,招來外面的衙役道:“替我去王府一趟,告訴常統領,我房里胡床下放著一個竹笥,請他取出來盡速給我送來。”
衙役一走,藺承佑也跟著起了,嚴司直不知何意:“怎麼了?”
“我覺得我們想岔了,嚴大哥,你先盤查剩下的人,我去小佛堂一趟。”
***
外面下起了雨,春雨綿綿,細如發,兜頭灑落下來,如的輕紗籠到臉上。
藺承佑冒雨回到小佛堂,相距老遠就看見殿燈火熒煌,門口站著兩名衙役,正隔窗往里張,回頭看到藺承佑,齊聲道:“人都在里頭。”
藺承佑一邊點頭,一邊快步進了小佛堂。
殿里滿是人,左邊四個坐姿七歪八斜,依次是見天、見仙、見樂和見。
猜你喜歡
-
完結1962 章

腹黑狂妃︰絕色大小姐
殺手?特工?天才?她都不是,她是笑顏如花、腹黑兇猛、狡猾如狐的蘭府家主。 想毀她清白的,被剁掉小指扔出去喂狗;想霸她家業的,被逼死在宗廟大殿;想黑她名節,讓她嫁不出去? sorry,她一不小心搞定了權傾天下、酷炫狂霸拽的攝政王大人! 他︰“夫人,外面盛傳我懼內!” 她眨巴眨巴眼楮,一臉無辜︰“哪個不長眼的亂嚼舌根,拉出去砍了!” 他︰“我!” 她︰“……”
180.4萬字8.09 132274 -
完結137 章

招魂
-落魄的閨閣小姐X死去的少年將軍-從五陵年少到叛國佞臣,徐鶴雪一生之罪惡罄竹難書。即便他已服罪身死十五年,大齊市井之間也仍有人談論他的舊聞,唾棄他的惡行。倪素從沒想過,徐鶴雪死去的第十五年,她會在茫茫雪野裡遇見他。沒有傳聞中那般凶神惡煞,更不是身長數丈,青面獠牙。他身上穿著她方才燒成灰燼的那件玄黑氅衣,提著一盞孤燈,風不動衣,雪不落肩,赤足走到她的面前:“你是誰?”倪素無數次後悔,如果早知那件衣裳是給徐鶴雪的,她一定不會燃起那盆火。可是後來,兄長失踪,宅田被佔,倪素跌落塵泥,最為狼狽不堪之時,身邊也只有孤魂徐鶴雪相伴。 伴她咬牙從泥濘里站起身,挺直腰,尋兄長,討公道。伴她雨雪,冬與春。倪素心願得償,與徐鶴雪分道揚鑣的那日,她身披嫁衣將要嫁給一位家世,姿儀,氣度都很好的求娶者。然而當夜,孤魂徐鶴雪坐在滿是霜華的樹蔭裡,看見那個一身紅的姑娘抱了滿懷的香燭不畏風雪跑來。“不成親了?”“要的。”徐鶴雪繃緊下頜,側過臉不欲再與她說話。然而樹下的姑娘仰望著他,沾了滿鬢雪水:“徐鶴雪,我有很多香燭,我可以養你很久,也不懼人鬼殊途,我們就如此一生,好不好?”——寒衣招魂,共我一生。 是救贖文,he。
50.1萬字8 22374 -
完結609 章
毒后歸來之鳳還朝
一朝錯愛,她為薄情郎擦劍指路,卻為他人做了嫁衣,落了個不得好死的下場。上蒼有眼,給了她一次重新開始的機會。這一次,有恩報恩,有仇報仇,她手持利刃,腳踏枯骨,鳳回天下。看慣了人們驚恐的目光,她本想孑然一生,卻陰差陽錯被個傻子絆住了腳步。這世上,竟真有不怕她的人?逆流而上,他不顧一切的握住了她的手。
153.9萬字8 14787 -
完結36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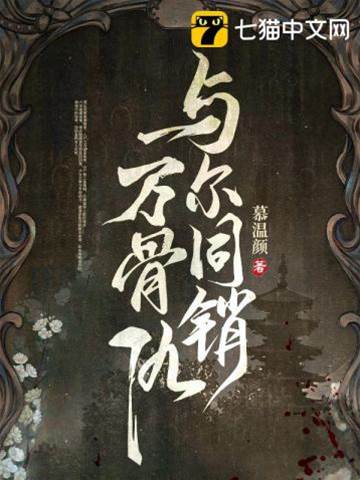
與爾同銷萬骨仇
深山荒野狐狸娶親,人屍之內竟是魚骨,女屍愛上盜墓賊,吊滿詭異人影的地宮...... 六宗詭譎命案,背後隱藏著更邪惡的陰謀。 少女天師與年輕尚書,循著陰陽異路解決命案,卻每每殊途同歸。 暗夜中的枯骨,你的悲鳴有人在聽。
32.6萬字8 7479 -
完結508 章

嫁給瘋批太子衝喜後
慕家不受寵的嫡女,被一道聖旨賜婚給命在旦夕的太子周璟沖喜。 不少人看笑話,可別把人給衝死在榻上。 周璟一睜眼,就多了個未婚妻。 小姑娘明明很怕他,卻還是忍不住的表忠心:“殿下,我會對你很好的。” “殿下,你去後我定多多燒紙錢,再爲您燒幾個美婢紙人。” “殿下,我會恪守婦道,日日緬懷亡夫!” 陰暗扭曲又裝病的瘋批周璟:…… 很久沒見上趕着找死的人了。 成親那天,鑼鼓喧天。 數百名刺客湧入隊伍,半柱香前還在裝模作樣咳血的太子劍氣淩厲,哪還有半點虛弱的樣子? 周璟提著沾血的劍,一步步走至嚇得花容失色的她跟前,擦去濺落她右側臉頰的血,低低似在為難:“哭什麽,是他們嚇著你了?”
84.6萬字8.18 14349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