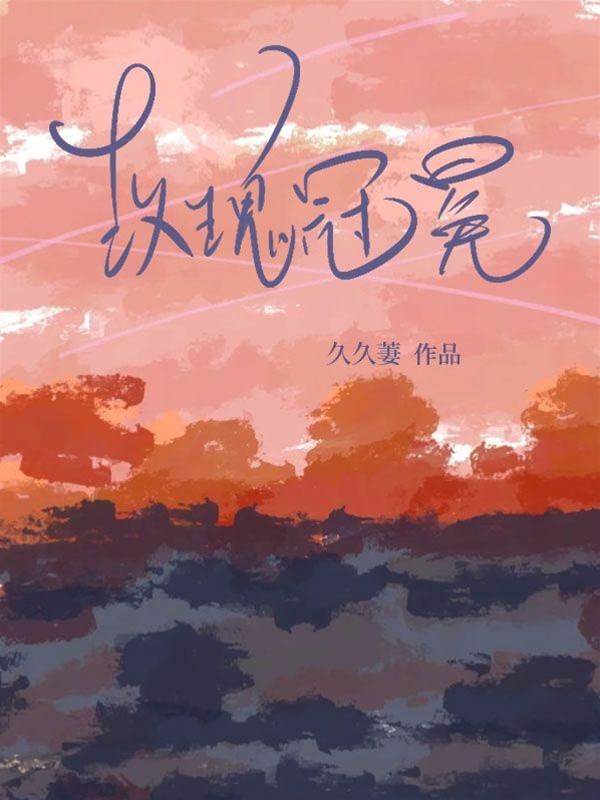《暗黑系暖婚》 第二卷 290:時瑾當采花賊,霍隊中槍(二更)
募地彈開,半邊臉包著紗布,另半邊臉已經扭曲,眼睛全是驚慌恐懼:“我沒有殺人!我沒有詐騙!”
蔣凱懶得啰嗦,拽住:“等到了警局再說。”
手推搡,扭頭向徐平征求救:“爸!”
“爸,救我!”
“我是冤枉的。”掙扎間,頭發散,臉上的紗布也被掙開了,右邊臉頰上一條手指長的傷疤嫣紅,新長出來的疙瘩凸出,形狀像極了蜈蚣,徐蓁蓁一張,便猙獰地蠕。
蓬頭垢面,狼狽不堪。
滿場安靜,只有徐蓁蓁呼天搶地的求救聲:“爸,我是您的兒,你救救我!”
“爸——”
推推搡搡就是不肯走,一雙手在蔣凱上胡揮舞,湯正義見人不老實,直接過去,拷上了手銬,把人拖走,作一氣呵,毫不拖泥帶水。
“爸!”
“爺爺!”
徐平征擰著眉,有幾分痛心,別開眼,沒有再看。徐老爺子也什麼都沒說,只是對賓客致歉。
到底怎麼一回事,在場的也都看明白了,假千金詐騙冒充,真千金認祖歸宗,這種戲碼,在豪門權貴里不是什麼稀罕事,只是沒想到素來家風嚴謹的徐家,也會有這檔子狗之事。
誒,說來姜九笙也是好命,有時瑾這個男朋友,現在又多了徐家這層關系,以后在華夏七省都可以橫著走了。
不過,從頭到尾,姜九笙都寵辱不驚,不置一詞,淡淡然地觀,不喜也不怒,不驚還不懼,這份心也確實有徐家的風骨。
散場后,徐家的七大姑八大姨都圍過去,瞧著姜九笙,好生歡喜,這才是徐家人嘛,多順眼。徐老爺子一直咧著,領著姜九笙去認親戚,平時一個個在場商場都端著不茍言笑與一本正經,這會兒,一個個樂得跟個傻子似的。
Advertisement
姜九笙有點不適應,子慢熱又冷清,只能盡量禮貌周到。
時瑾了眉,正想把帶走,電話響了,是陌生的號碼。
他接聽:“喂。”
是刑偵一隊的周肖,聲音有點發抖:“時醫生嗎?”
時瑾道:“我是時瑾。”
那邊語氣又急又快,說了個大概。
時瑾掛了電話,也不管徐家的人,上前去把姜九笙牽到邊,蹙著眉頭同說:“笙笙,我有急病人。”
姜九笙點頭:“你去吧,不用擔心我。”
一旁的徐老爺子一聽,趕見針,一臉期待的小表,甚是生:“笙笙,你今晚跟爺爺回家住不?”
姜九笙在遲疑。
老爺子表一變,憂傷極了,長長嘆一口氣:“誒,發生這麼大事,我心里難過啊,也這麼大年紀了,不知道晚上還能不能睡得著。”說著,他作勢要抹眼淚,做出又心酸又可憐的表,“要是有個人能陪我說說話解解悶就好了,瑟瑟也不在家,我一個孤家寡人,誒!”
后,徐家一群小輩一致覺得,老爺子可以出道了,演技派,老戲骨。
姜九笙哭笑不得,不好再拂了老人家的意:“我今晚回徐家。”
老爺子樂呵了。
時瑾隨,只說:“手結束后我過去。”
老爺子瞬間不開心了。
還有更過分的,時瑾低頭在姜九笙臉上親了一下才走。
老爺子郁卒!
現在的男人真特麼浪!當眾親別人家的小姑娘,不要臉!
九點四十,秦氏酒店門口停了一輛救護車,四周全是帶槍的警察,剛從拍賣會上出來的賓客,一見這陣勢,都自覺繞道。
周肖站在救護車旁,焦急地頻頻看向酒店大門,一見時瑾出來,立馬上前去:“時醫生。”
Advertisement
時瑾頷首,問急救的護士:“人怎麼樣?”
來的是天北醫院急救科的人,見時瑾,立馬回話:“槍傷,左口十厘米,心跳溫都偏低,生命征不太好。”
“意識。”
護士回:“意識還是清醒的。”
時瑾上了救護車,周肖一頭大汗,也跟著上去了,刑偵一隊幾個都要上去,被時瑾回頭一個不冷不熱的眼神制止了。
救護車開了。
“時醫生,”周肖一副看救世主的表,看著時瑾,眼睛紅通通的,跟哭了似的,“你一定要救救我們隊長。”
一個大老爺們,還帶著哭腔。
也不怪周肖會哭,這一槍本來是該他挨的,當時他跟著緝毒隊的林隊最先闖進窩點,林隊一槍鎮住了一屋子的毒販子,沒想到有人在地上藏了一把槍,距離太近,地方也小,他閃躲不及,是霍一寧在后面推了他一把。
救護車里,霍一寧躺著,由護士著傷口,他白著一張俊臉罵:“別哭喪著臉,老子還沒死呢。”
周肖梗著脖子:“誰讓你推我了!”
媽的!
霍一寧頂了頂牙:“老子手賤!”
可不就是手賤,腦子里一直告誡自己,要惜命,可真到了千鈞一發的時候,跟條件反似的,還沒仔細想,就做出了第一反應。
“還有力氣罵人,傷得應該不重。”時瑾瞥了一眼,拿了雙手套戴上,護士讓開位置,他蹲下,看了看霍一寧口的傷。
已經止住了。
霍一寧出了很多汗,臉上一點都沒有,聲音倒四平八穩:“是5。8MMNagant子彈頭,程500M,槍口初能13000J。”
這種槍支,殺傷力不算大。
時瑾用手電照了照霍一寧的瞳孔,往后退了一些,他出另一只手,強打在手上,問:“這是幾?”
Advertisement
他戴著醫用的塑膠白手套,手指骨節的廓分明,照下,有些剔。
霍一寧瞇了瞇眼睛,回答:“四。”
瞳孔不聚,目眩。
時瑾轉頭,對一旁護士道:“ChitosanXStatSyringe,40mg。”
護士立馬取藥,做急注。
一針下去,霍一寧就昏過去了。
周肖心肝一抖,悲痛絕得喊了幾聲‘隊長’:“時醫生,我們隊長不會有事吧。”
時瑾戴上口罩,拿了把剪刀,不疾不徐地將霍一寧的服剪開:“離心臟四厘米,死不了。”沒抬頭,專注地出兩指,在霍一寧傷口旁輕按。
斜上而,深六厘米,拿槍的人應該是蹲著的。
時瑾手指往下,輕探,找到了,子彈的位置,他起,把沾了的手套取下:“通知麻醉科和科,二十分鐘后手。”
十點半,景瑟還在楓城影視基地拍戲,一晚上只有兩場戲,不過,演技是實打實的差,和男主演默契為零,兩場戲,三個小時下來,還沒結束,導演扶額,已經不記得第多次NG了,不向自己發出了來自靈魂深的拷問,為什麼要用景瑟這個高級花瓶啊。
哦,景家投了錢,還不。
誒,影視圈的規則啊,誰是金主誰說了算。罷了罷了,今天就到這里吧,反正好拍歹拍也就這樣了,演技突破不可能,這輩子都不可能。
導演擺擺手,讓大家收工。
景瑟乖巧地和工作人員說辛苦了,和黑著臉NG到吐的男主角說明天見,剛走出鏡頭,陳湘立馬跑過去:“瑟瑟。”一副‘出大事了’的表。
景瑟不解地看。
陳湘語氣沉重:“剛剛刑偵隊的人來電話了,說是,”不知道該不該說,明天景瑟還有一整天的戲,不過也就糾結了一下,“霍隊傷了。”
Advertisement
景瑟一聽,小臉就白了,子一晃,扶著陳湘,快哭了:“湘姐,你給我訂飛機票。”說,“我手哆嗦。”
是在哆嗦,渾都哆嗦。
這要哭又忍著不哭的樣子,可憐兮兮的。陳湘想,霍一寧要真有個三長兩短,這小姑娘估計也要跟著廢了。
陳湘扶著坐下:“我剛剛查了,最快的航班也要等凌晨后。”
凌晨后?
不行,現在腦子里就停不下來各種生離死別的腦補,就那麼幾十秒里,連殉葬的心思都有了,就差選墓地了。
呼吸不過來,大口了幾口氣,哆嗦著手,到手機,撥了景爸爸的電話,接通后,著聲兒:“爸爸,我是瑟瑟。”
景爸爸一聽這聲兒立馬從床上彈起來:“怎麼了,寶貝?”
景瑟吸吸鼻子,哽咽:“我家隊長傷了,你快給我搞一架飛機來。”
隊長?
哦,警局那個小子。
景爸爸一聽兒這哭腔,心都疼碎了:“寶貝你別哭啊,爸爸這就去給你搞。”別說搞飛機,就是搞星星搞月亮也得搞來。他寶貝兒長這麼大,就沒怎麼哭過,把他心疼的喲。
景瑟淚珠子直掉,哭著催景爸爸:“你快點,不然我就要哭了。”
“……”
景爸爸趕爬起來,把三個書全部起來,立馬搞飛機來!
凌晨一點,手結束。
時瑾剛回辦公室,桌上的手機便響了,他看了一眼,七個未接,是秦行的號碼。
“喂。”剛出手室,上的無菌還沒有換下,有淡淡的味,混著消毒水的藥味,他攏了攏眉,忍住胃里的反。
一接通,秦行便問:“怎麼才接電話?”
時瑾道:“在手。”
秦行似乎正在氣頭上,火氣很大:“趕來一趟秦家,我們的一批貨又被截了。”
看來秦明立已經連夜趕回去了。
時瑾神不變,低眸,角沾的映進眼里,瞳孔與眼角都微微泛紅,清潤的眸在夜里融了,鷙了幾分:“那批貨是秦明立負責,善后與滅口的攤子讓他自己收。”
秦家素來如此。
所有地下易都互不叉,有許多易支線,若是哪條線暴了,第一時間滅掉那條線上所有可能連累到秦家的活口,連供貨商都放過。
正因如此,警方這麼多年都沒有抓到秦家的把柄。
秦行不滿時瑾不冷不熱的態度:“不管是誰負責,都是我們秦家的事,你是秦家當家,你不做主誰做主。”
辦公室里燈昏暗,時瑾目深沉,比月冷,沉默須臾,他道:“要真是我當家做主,我第一個撤了秦明立。”
秦行無話可說了,至目前,他不敢完全放權,需要有人牽制時瑾。
電話被掛斷,秦行抬眸:“剩下的爛攤子你自己收,要是把秦家牽扯出來了,這局子你也自己蹲。”
他表明了態度,棄車保帥。
秦家一貫如此,不會為了一個分支而搖本,若是這個分支暴了,就整個砍掉,若是秦明立暴了,也一樣毫不猶豫地棄掉。
秦明立低頭,拳頭握:“我知道了,會理好這件事。”
秦行思忖了片刻:“地下易的事,你暫時都不要手了。”
這是要削權。
秦家目前大部分易都在時瑾手里,最重要的部分秦行自己握著,秦明立手里不到三。
他喊:“父親!”
秦行態度沒有毫緩和:“留在你手里你也保不住,那幾條線不能再被剿了。”
這個兒子,終究魄力與能力不夠。
這是要棄了他這張牌,秦明立立馬力爭:“父親,難道你不覺得蹊蹺嗎?每一次易都剛好有警察過來,我們秦家這近半年里,前后損失了四條支線,九個供貨商,我懷疑我們秦家里面有警方的鬼。”
秦行沉。
確實如此,秦家近半年,頻頻出事。
秦明立知道他猶豫了,立刻表態:“懇請父親再給我一段時間,我一定把這個叛徒抓出來。”
凌晨一點半,時瑾的車停在了徐家門外,秋夜漸涼,一盤圓月高掛枝頭。
這個點,徐家人都睡了,大概還有人外出未歸,留了一個幫傭的阿姨在守門,見是時瑾,趕去開門:“時先生。”
他進去,問:“笙笙在哪間房?”
“笙笙小姐已經睡了。”
大廳的樓梯口,睡著一只貓,聽聞聲音,聲了一句,夜里一雙湛藍的眼睛發,探出腦袋來,一見是時瑾,立馬安靜了。
這只貓是認得博的爸爸的,很怕很怕他。
“帶我過去。”
幫傭阿姨期期艾艾,回了時瑾的話:“老爺子吩咐了,說笙笙小姐累了,任何人都不要去打擾。”
老爺子的原話其實更直白:千萬別讓時瑾那只大尾狼進了笙笙的房間!
“客房已經準備好了,要我帶您過去嗎?”
時瑾點頭,沒說什麼。
凌晨一點五十,徐青舶回徐家。
他已經連著值班了一個禮拜,本來他這種級別的醫生,本不用值夜班,他是替科室的夏醫生值班,為什麼要替夏醫生值班?
因為夏醫生代替他去了非洲醫療救援隊。
丫的,非洲醫療隊是跟他杠上了,幾次調他過去,還好他機智躲過了,找了個替死鬼。
別墅外面的路燈亮著,徐青舶有點頭重腳輕,了眉心往屋里走,突然,目掃到斜上方四十五度。
他頓時停下,看了幾眼,居然有人在爬窗,那背影……勾了勾角,拿出手機,撥了老蔣的電話:“拿子出來,抓賊。”
不消一會兒,老蔣穿著背心,手里拿了個手臂的子,四下張:“在哪呢?賊在哪?”
徐青舶抱著手,抬抬下:“那上面。”
老蔣抬頭一看,二樓窗戶上果然有個人,他大喝一聲:“誰在上面,也不看看什麼地方,做賊都做到徐家來了!”
這一聲,把客廳里的貓都喊醒了,一直喵喵。
那個‘賊’站在兩間房相連的小臺上,形修長,不疾不徐地回頭:“是我。”
這聲音……
“時、時醫生?”老蔣懷疑自己耳背了,用手電筒仔細照著,撐了撐老花鏡瞧了又瞧。
“拿開。”聲音冷,而且清,“手電筒。”
一只白皙似玉的手擋在眼前,遮住刺目的,五指修長,骨節分明,指如削蔥,在淡淡夜里,十分漂亮。
是時瑾。
徐青舶笑出了聲:“原來是采花賊啊。”
老蔣:“……”
猜你喜歡
-
完結307 章
名門夫人:寵妻成癮
她,藍氏財團的二千金,讓人無比羨慕的富二代,隨便說幾個相識的人名出來,都是讓人趨之若鶩的人物,可是男友結婚,新娘竟然不是她,這般高貴的她慘遭拋棄。 他,千尋集團當家總裁,財勢逼人的霍家大少爺,標準的富二代,權二代,在t市是個隻手可遮天的大人物,誰知道結婚日子挑好了,卻在登記當天,新娘逃婚,他也慘遭拋棄。 可笑的是,他是她準姐夫。 看到憤怒而落寞的準姐夫,她忽然嘲笑著:「我們都是被拋棄的人,剛好湊成一對。」 他抿唇不語。 隔天卻叫上她拿著戶口本到民政局辦了結婚手續,由她代...
165萬字8 70598 -
連載1257 章

奶包四歲半:下山后七個哥哥團寵我
粥粥天生缺錢命,把道觀吃窮後終於被趕下山討飯去了,卻一不小心找到了個長期飯票。 秦老夫人收養小粥粥後,立刻給小兒子發消息“看,你閨女!”“喜當爹”的秦冽面無表情“送走。”“喜當哥”的秦家小霸王們一臉嫌棄“不要,妹妹只會哭,不好玩。” 秦家的死對頭也都在等著看熱鬧,看粥粥什麼時候把秦家搞破產。 卻不想,秦冽每天簽單子簽到手軟,秦家蒸蒸日上,將首富的位子坐得更穩,就連秦家那個生來殘廢的七哥也能跑能跳了。 宴會上,秦家小霸王把粥粥圍成一團,一臉討好。 “妹妹,好吃的都給你!”“妹妹,今天想听什麼故事?哥哥給你講!” 秦冽徑直走過來,把小姑娘抱在懷裡,目光冷冷掃過幾個侄子,宣布所有權“我女兒!”
233.2萬字8.31 70292 -
完結191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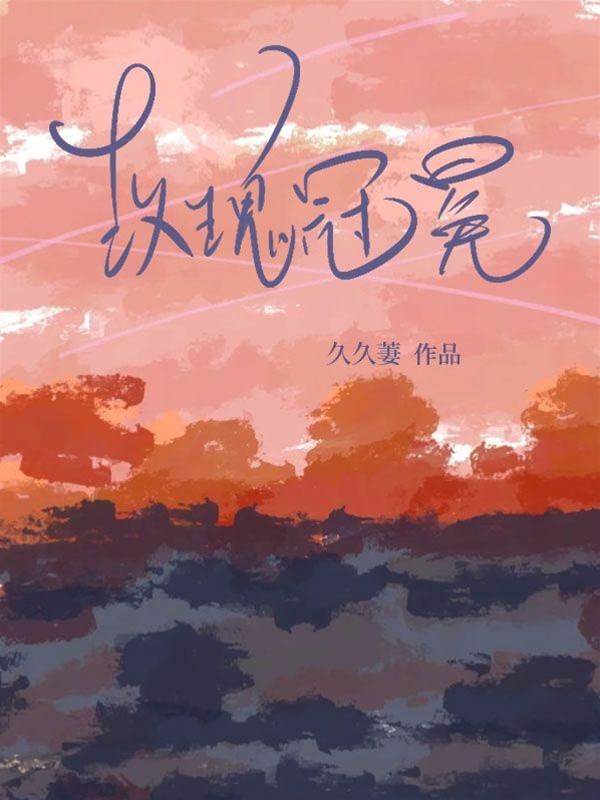
玫瑰冠冕
【先婚後愛?暗戀?追妻火葬場女主不回頭?雙潔】她是徐家的養女,是周越添的小尾巴,她從小到大都跟著他,直到二十四歲這年,她聽到他說——“徐家的養女而已,我怎麼會真的把她放在心上,咱們這種人家,還是要門當戶對。”-樓阮徹底消失後,周越添到處找她,可卻再也找不到她了。-再次相見,他看到她拉著一身黑的少年走進徐家家門,臉上帶著明亮的笑。周越添一把拉住她,紅著眼眶問道,“軟軟,你還要不要我……”白軟乖巧的小姑娘還沒說話,她身旁的人便斜睨過來,雪白的喉結輕滾,笑得懶散,“這位先生,如果你不想今天在警局過夜,就先鬆開我太太的手腕。”*女主視角先婚後愛/男主視角多年暗戀成真【偏愛你的人可能會晚,但一定會來。】*缺愛的女孩終於等到了獨一無二的偏愛。
33.4萬字8 57966 -
完結148 章

強扭的校草酸又澀,重生她不追了
(重生+1v1雙潔雙初+追妻火葬場)前世,蘇迦妮對校草一見鐘情,追他好幾年沒追到,最后靠卑劣手段母憑子貴,成了他的妻子。她深知他不愛,她漸漸心灰意冷。重生回到高考前。她不再纏著他講習題,考了高分,也不填他保送的清大,她不追他了。同學聚會。他卻將她堵在墻角,語氣冰冷,“躲我?”-關于人設:蘇迦妮,膚白貌美,腰軟聲嗲,前世是軟磨硬泡無臉無畏的犟種戀愛腦,重生后恐戀恐婚恐遲域。遲域,高冷學霸,禁欲系校草,京圈太子爺,800個心眼偏執狂,獨占欲強。-后來,她酸軟著腿從遲域懷里醒來,看到手上多出來的求婚鉆戒,嚇得連夜跑路。再后來,他猩紅著眼擁緊她,“蘇迦妮,再跑弄死你”
25.4萬字8.25 19103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