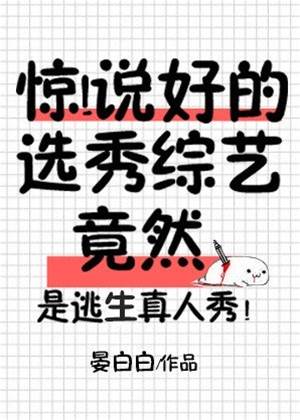《寧為長生》 [寧為長生] - 第3章 藏龍臥虎
午間用飯的時候,朱定北才意識到這不起眼的黃品小學堂里竟還藏著好幾個人。
他后那個虎頭虎腦的小家伙自報家門時他還吃了一驚,再到雙胞胎人手一個拉著兩個小伙伴過來表明了份后,他看這些家伙的眼睛就奇怪了。
別管介紹人說得多好聽,黃品說白了都是些“笨”腦袋。一個學階幾百學子,天地玄三品都有甲乙丙丁數個學堂,單只黃品獨設一個學堂,可見就是幾百號人里讀書最笨的子弟集中營,這可不是什麼彩事。
工部尚書的雙胞胎在這里尚且還能理解,畢竟后來這兩個孩子子承祖業,在工學的造詣上青出于藍。他們醉心工,學上不經心以至于落于人后不算奇怪。但連秦大統領的長孫,中書令的十一子和長信侯府正經襲爵的寧小侯爺都在黃品學堂,實在讓人費解。
軍政分明,互不干涉。朱定北前生雖說不是對朝政漠不關心,但結的人之又,哪怕一二個打過照面,卻因為常年不在京城也沒有什麼。
不過能讓他記住名字的,都是在京城有名有姓更有一番作為的人。
工部尚書樓敬知的雙胞孫兒,軍統領秦孝先的長孫,中書令賈惜福的第十一子,不說他們赫赫有名的父輩,他們自己及冠后的風采可不曾埋沒在父輩的環下。
再有這位曾讓老爹都說過捉不手段厲害的長信侯……這家伙生父早亡,祖父也沒撐過幾年,以三歲稚齡承襲長信侯爵位還沒教長信侯府在這滿是紛爭的京沒落,只說這一點,便知道是個厲害的。
朱定北不由多看了幾眼在自己對面安靜吃飯的孩子,除了個頭比同齡人大了一倍,實在沒看出什麼不同來。
Advertisement
想是被他看得久了,寧衡抬起頭,過于清澈的視線與朱定北打量的目撞在一起,惹得朱定北退了下。
這小子大概想不明白這個新來的孩子為什麼盯著自己看,半晌,幾乎在朱定北被他看得定力都要用完的時候,突然從自己的飯盒中夾出一塊紅燒,放到朱定北的飯碗中。
“……”
朱定北覺得自己的表空白了一瞬。見寧衡直勾勾地看著自己,沉默了一會兒,還是默不作聲地把那塊紅燒夾起,放到里。
眼看著寧衡像完了一件大事,如釋重負地低頭重新吃自己的飯菜,朱定北突然有種覺:……果然像老爹說的,這小王八羔子心思詭異,他們這種人對付不來啊。
國子學自先□□那代就開始辦起來,這百年來吸納了很多學子,目前還未對平民開放,能夠進來求學的都是宦子弟。
這些人家的條件自不會差,國子學并不供應學子的飯食,他們帶來的食無不致可口,花樣齊全。相比起來,朱定北這份飯菜就顯得寒酸了。
老夫人也沒有準備這些的經驗,一切都按朱定北平時在家的吃食來。謹記著太醫的囑咐,鎮北侯府對于朱定北的膳食都以清淡為主,一則他還在調養的階段,再則也怕他飲食沖突水土不服弄出什麼病癥來。
心的小伙伴們經過這一幕,紛紛留意到朱·小可憐·定北的吃食,忍痛割將自己最吃的那份食夾到朱定北飯碗里,眼地看著他吃下去,才一臉被自己得要流淚的模樣收回視線。
朱定北:“……”
書與學子不同席,雖然朱定北對朱水生從沒分過這些,但畢竟鄉隨俗。
用過飯,早就狼吞虎咽吃完等在門外的朱水生迎了上來。警惕地看著和朱定北走在一道的人,亦步亦趨地跟在朱定北后護送他回學堂。
Advertisement
“小爺,這個下午用的蜂水,還有這個,你了要吃,是你最的餡。”小廝水生說不完的叮囑,朱定北好笑地了他兩頰的嬰兒,也問了他幾句,得知他一早上都用在蹲馬步上了,不由嘆了口氣。在這京城,不說自己,就是水生也像是被折斷翅膀的蒼鷹,要適應囚籠里的生活,除非篡改本。
朱定北諒他,并不拘束,讓他自己找事做。
不過他上次傷嚇壞了朱水生,里應下來,眼睛卻是恨不得分分秒秒黏在朱定北上不讓他有半分閃失,又怎麼可能拋開他自己玩耍呢。
從學堂到膳房相隔兩刻的步行路程,來去權當學子們的消食和消遣了。進了學堂雖然還未曾開課,學子們或是看書或是寫字,就連秦奚也坐的直直的,拿著一卷書簡強記背著什麼。
朱定北環視一眼,索趴在書桌上睡了起來。
他后的秦奚眼地看著他,很是羨慕,但想到阿爺虎目圓睜的樣子……秦奚抖了抖,掐了掐自己的大,打起神來繼續背書。
撞鐘的聲音再次響起,朱定北嫌棄地了自己角可疑的潤,不甚滿意地看了眼書桌。趴著睡果然容易流口水,從前老娘原來不是唬弄他玩的。
朱定北不喜歡甜不拉幾的蜂水,但是老夫人的一番心意不能辜負,喝了幾口,了臉,下午講學的夫子便走了進來。
夫子說的是論語,不出一會兒工夫,就功地把朱定北推進了周公的懷抱,雙目無神地看著他。
好歹撐過了一天,回了家關心問起的老侯爺老夫人見他一臉不愿多談的樣子也沒有追問,當他過得不順心,只能安說讓他放松學,能學多是多,不要有負擔。
Advertisement
到了晚間,放心不下的老侯爺到孫子的小院瞧了一眼,見屋子里點了燈,孫子正干勁十足地看書,樂呵呵地走了。
“老爺,怎麼樣?”
“怕什麼?狗娘的鮮卑都被我們朱家人打得哭爹喊娘,幾本破書算什麼。”
老侯爺大手一揮,全然沒看見發妻鄙夷的神:真要這麼簡單,當初被一首詩為難地抓耳撓腮的又是哪個?
聽他表孫兒自有計較,老夫人也放心,不再多問。
第二日朱定北比昨日早了一個時辰出發,到國子學的時間尚早便在書院里逛了逛,順便探探地形悉環境。
路遇不臨湖依柳搖頭晃腦的學子,他都快走避開。
誠曰秀才遇到兵有理說不清,朱定北最怕就是這些酸儒,多和他們說上幾句話飯都要吃兩口。
到了學堂,沒想到長信侯爺已經坐在位置上。
瞧他那一臉專注的模樣和他書桌上那一本平生僅見的厚書,他沒忍住湊過去看了眼,竟是本醫書。
他就說嘛,能讓老爹都慨的人怎麼可能智力只到黃品,分明也是不務正業。
無端的,這個發現讓朱定北對寧衡多了兩分好。
不等和他搭上話,寧衡小心地收起醫書,解下書簍外掛著的一個小福袋,遞給他。
“給我的?”
朱定北忙不迭接過,拉開福袋一香味鋪面而來,他將油紙包好的餡餅拿出,忍不住吸了吸口水。這兩個月里簡直淡出鳥了,他這銅腸鐵胃,啃得了樹皮,喂得下雪球,平生無不歡。若不是長者賜不忍辭,也不會乖乖這麼久清粥小菜的荼毒。
啥也不多說了,他一口塞進里,抬手拍了拍寧衡的肩膀,含糊嚷道:“一飯之恩,小弟銘記于心,他日必當涌泉相報!”
Advertisement
寧衡余掃了眼他油膩的手指,視線落在他無比滿足的臉上,垂了垂眼眸。
朱定北昨日沒留心,今日特意問過水生學堂的課程。
講學階段的課程是按照六藝而設:禮,樂,,,書,數。
禮所學除了各種日常禮節之外,更多的是孝悌友德信這些做人本。樂雖則要求每個學生至選取一門,但選擇權則給了學生自由,有專門的樂夫子教導。和則是朱定北的專項,朱家軍的帥騎功夫在軍中的對手可沒有幾個。
再有便是書,除了詩書典籍和書法之外,同樣也講學一些縣志史學,畢竟講學還不像進學和大學那樣針對科舉或實務,了些刻板。至于數,涉獵就廣了,一般而言除了九章算之外,夫子還會講一些淺顯的天文地理,以及數在諸如水利等各方各面中的運用。
這日上午便是禮課。背誦一章孝經,再聽夫子口若懸河如數家珍地列舉由古至今一些人至深至至的人故事,加上夫子煽極強的口才,學堂上的學子們目炯炯有神全神貫注。朱定北最煩說教,夫子的聲音猶如洪鐘,在他半夢半醒間鐺地一聲,驚地坐直,如此反復。
到了下午,朱定北總算活了過來。
講學的校場不大,一眼去陳列的靶子和弓箭都盡收眼底。大部分學子顯然興致缺缺,只因武夫子一上來便要求蹲一炷香的馬步。
烈日炎炎,再有夫子放在每個人屁下的香,雖然據經驗人士說明這一屁坐下去燃香不至于燙疼屁,但也有丟臉至極,只能咬牙忍了。
也是為難了這些四不勤的學子,武夫子要求對他們可沒有半點放松,若是懶或是作不到位,輕則糾正,重則點名怒斥加點一炷香。汗水滴到眼睛里都不敢,雙抖抖索索比著站在冰雪天里都厲害,只能憑著意志力強撐。
朱定北會不到他們的心酸,一炷香的馬步對他而言實在太輕松。
他老爹朱元帥不輕易打罵孩子,讓他不順心了卻也決不讓你舒坦,罰蹲馬步輒一個時辰小半天,朱定北從小罰到現在,結束的時候還覺得有些不過癮。
秦奚看出來了,取弓箭的時候湊上來親熱地說道:“你家元帥爹爹也經常罰你蹲馬步?”
將門虎子大概都有差不多的年經歷,秦奚到國子學教這麼久還是第一次遇到同類,說不出的親近。見朱定北果然出一副心有戚戚的苦臉,拍了拍他的臉,一副過來人的臉道:“以后你就知道這是為你好了。你看我現在,頭上頂盆水也能蹲一個時辰都不抖一下,他們還沒有人能贏過我呢!”
朱定北沒能準確明白此人的驕傲點在哪里,便了他的大耳朵,語重心長道:“再接再厲。”
平靜安詳的日子一劃而過,直到朱定北再一次在詩書課上以頭搶桌,脾氣火的夫子終于發。
教執重重地砸在書桌上,夫子怒道:“把老夫剛剛說的這一段背誦一遍!”
看朱小侯爺兩眼無神一臉蒙圈,夫子胡子都翹起來了,“朽木!不會還不好好聽講,你看看誰有你這樣頑劣?若是周公能教會你這些,你費什麼功夫來我這里?真真氣煞老夫也,劣,你莫不以為自己是再世宰予嗎?”
朱小侯爺了眼睛站起來,一臉不明白狀況的模樣。
憋笑的課堂詭異地嚴肅,不知誰突然嘀咕了一聲,“我好幾次看到他睜著眼睛睡覺啦,再世宰豬,非他莫屬。”
“噗”的一聲,整個課堂哄然大笑。
猜你喜歡
-
完結264 章
老公,餓餓,飯飯
齐澄不知道自己穿的是生子文 只知道他是恶毒反派炮灰 是阴冷偏执反派boss的男妻子 齐澄穿来后 望着眼前的大别墅 不限额度的黑卡零花钱 以及坐在轮椅上大反派的绝美侧脸 不是,软饭它不香吗? 为什么非齐澄不知道自己穿的是生子文 只知道他是恶毒反派炮灰 是阴冷偏执反派boss的男妻子 齐澄穿来后 望着眼前的大别墅 不限额度的黑卡零花钱 以及坐在轮椅上大反派的绝美侧脸 不是,软饭它不香吗? 为什么非要离婚 做主角攻受神仙爱情的炮灰? 老公,饿饿,饭饭! “他腿也不方便,也不会发生那什么关系,就是护工工作,我会尽职尽责吃软饭的!” “老、老公,我来帮你擦身体吧。” 白宗殷:…… 后来 齐澄才知道自己名字另一层意思要离婚 做主角攻受神仙爱情的炮灰? 老公,饿饿,饭饭! “他腿也不方便,也不会发生那什么关系,就是护工工作,我会尽职尽责吃软饭的!” “老、老公,我来帮你擦身体吧。” 白宗殷:…… 后来 齐澄才知道自己名字另一层意思
57萬字8 12143 -
完結171 章
套路敵國皇帝后我懷崽了
鄀王爺江懷楚為了保護自己的國家 想和敵國皇帝聯姻 於是他隱去真實身份潛入敵國,考上了敵國狀元,千方百計接近敵國皇帝 * 瓊林宴上,新科狀元郎被人下了藥,意識迷離地往陛下懷裡鑽 面如冠玉,清絕端方 蕭昀坐懷不亂,不動聲色地笑納了一個吻,然後……毫不留情地推開了他 狀元郎見人離開,眨眼換了副冷淡至極的面孔 * 狀元郎清醒後,感念陛下柳下惠的“高尚”行徑,百般“回報” 無微不至地照顧他,卻連手指都不讓碰 端方矜持、清雅容華的狀元郎天天在眼跟前晃 蕭昀逐漸忍無可忍 * 狀元郎是敵國奸細,人還不見了 蕭昀遍尋無果後,一怒之下兵臨敵國要人 兩軍對峙,旌旗飄蕩,呼聲震天 敵國聞名天下的小王爺被人仔細扶著登上城牆,迎風而立 ……肚子有點凸 城下蕭昀抬頭瞥了一眼,神情一滯 又瞥了一眼:“退兵!快給老子退兵!”
37萬字8.09 8732 -
完結270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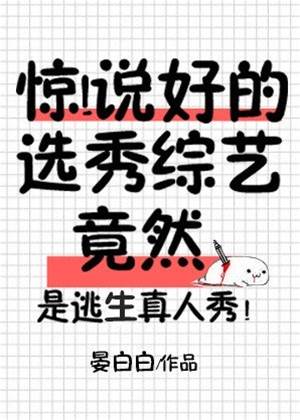
驚!說好的選秀綜藝竟然
某娛樂公司練習生巫瑾,長了一張絕世美人臉,就算坐著不動都能C位出道。 在報名某選秀綜藝後,閃亮的星途正在向他招手—— 巫瑾:等等,這節目怎麼跟說好的不一樣?不是蹦蹦跳跳唱唱歌嗎?為什麼要送我去荒郊野外…… 節目PD:百年難得一遇的顏值型選手啊,節目組的收視率就靠你拯救了! 巫瑾:……我好像走錯節目了。等等,這不是偶像選秀,這是搏殺逃生真人秀啊啊啊! 十個月後,被扔進節目組的小可愛—— 變成了人間兇器。 副本升級流,輕微娛樂圈,秒天秒地攻 X 小可愛進化秒天秒地受,主受。
89.5萬字8 8616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