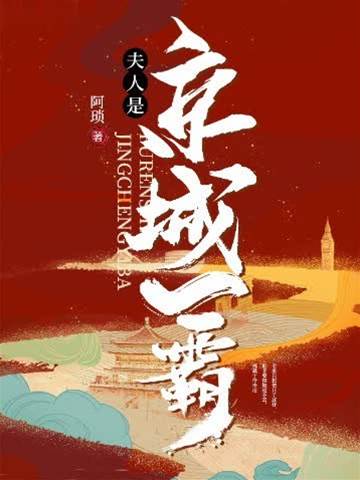《延禧攻略》 第五十八章苦與甜
數日後——
「那賤婢呢?」
葉天士正在收拾桌上的醫箱,聽了這話,回頭去:「皇上,您是說瓔珞姑娘嗎?」
「除了,還有誰?」帳幔後影影綽綽一個人影,冰冷如霜道,「把來,朕要親手剝了的皮!」
皇後坐在床沿,手中端著一隻盛著褐葯的瓷碗,葯略燙,不斷攪著手中的湯勺給之降溫,聞言抬頭一笑:「皇上,瓔珞是為了給您治病,才會口出狂言,現在皇上清了痰,神大好,以臣妾來看,瓔珞不但無過,反而有功。」
「……那臭丫頭給你灌了什麼**湯,你這樣都相信的話?」弘曆冷冷道,「依朕看,那些話若非早就藏在心裡,能那麼順溜的說完嗎?分明是借給朕治病的機會,變著法兒地出氣泄憤!」
皇後嘆了口氣:「就算皇上現在想找人算賬,隻怕也不行了。」
弘曆忽然沉默下來,帳幔遮去了他此刻的表,隻有因病而形銷骨立的側影倒映在帳子上,良久才言:「……為什麼?」
「瓔珞一回去就發了高燒,上起了大片紅疹,葉大夫說,是照顧皇上的時候染了病,如今再也支撐不住,倒下了。」皇後抬手撥開眼前的帳幔,「哪怕瓔珞有千萬個不好,看在心侍候,又染惡疾的份上,皇上也不該怪一時失言啊!若不然,將來還有誰會鞠躬盡瘁,拚力伺候呢?」
帳後出弘曆陷沉思的臉,他忽轉過臉來,沉沉對皇後一笑:「好,朕不怪,不但不怪,還要好好賞賜……」
養心殿耳房,幾名宮送來了弘曆的賞賜。
「這,這是……」魏瓔珞半窩在床上,看著對方手裡端著的黑湯藥,眼角忍不住了。
Advertisement
「瓔珞姑娘,這是皇上囑葉大夫特意為你開的葯,快喝葯吧!」宮走到床沿,一個將扶起,一個將盛葯的勺子遞到邊。
皇上所賜,哪能推辭。
魏瓔珞隻能極不願的喝了一口,結果哇的一聲,吃進多吐出多,一隻手卡著嗓子咳嗽了半天,才驚恐道:「怎,怎麼這樣苦,裡麵放了什麼東西?」
宮老實回道:「黃連。」
魏瓔珞立覺不對:「葉大夫給皇上開的葯裡麵沒有黃連啊!」
宮:「皇上那份沒有,但葉大夫給您開的藥方,一定得有。」
魏瓔珞驚愕道:「為什麼?」
「特傳皇上的話。」宮麵無表,魏瓔珞卻覺得自己能過對方的話,看見一張斤斤計較的臉,「黃連清熱燥,瀉火解毒啊!」
「……能不喝嗎?」魏瓔珞心驚膽戰看著那滿滿一大碗黃連湯。
「伺候瓔珞姑娘用藥。」宮以實際行回應了。
同一時刻,養心殿寢殿。
葉天士侍奉在弘曆旁,手中同樣一隻葯碗,裡頭盛著相似的葯,隻是獨一味黃連。
饒是如此,弘曆仍喝的眉頭皺,似為了減自己的痛苦,遂開口問道:「葉天士,那丫頭喝葯了嗎?」
皇上的脾氣真是來得快,去得也快,早上還是賤婢呢,晚上就了那丫頭,到了明天還不知道會變什麼。葉天士心裡轉著這個念頭,上則道:「有皇上口諭,自然是要喝葯的。不過,草民不明白,您為什麼要讓喝黃連呢?」
弘曆冷哼一聲:「這丫頭一肚子壞水,都能沁出毒來,黃連瀉火解毒,正適合!還有什麼對癥的中藥最苦?」
鬧起脾氣來,即便天子也如同一個凡人,還是個斤斤計較的小氣男人。葉天士隻能本著死同道不死貧道的心,小心回道:「要說最苦的中藥,黃連、木通、龍膽草,都是苦不堪言,最苦的是苦參——」
Advertisement
弘曆一擺手:「那就從今日開始,一天三頓,頓頓不同種類的苦藥,換著法子讓喝!要是不肯喝,就強行灌!良藥苦口利於病,朕這是為了救命恩人的命著想,你聽懂了嗎?」
「是。」葉天士應道。
「嗬嗬嗬嗬……」許是想到了對方邊喝邊吐的悲慘模樣,弘曆心大好,想著想著竟笑出聲來,葉天士的湯藥再送到他邊,他也不嫌難喝了,笑的全喝了下去。
葉天士見此,角了,卻不敢說什麼。
但得了弘曆這個指派,卻也不是什麼壞事,至他不必再想什麼理由,什麼藉口去探魏瓔珞了。
出了養心殿之後,他背著藥箱,馬不停蹄的來到側殿耳房。
宮人早已得到訊息,一路無人阻攔,他就這樣大搖大擺的走進房門,反手一關,對床上躺著的人影道:「魏姑娘,是我!」
原本氣若遊,病得氣息奄奄的魏瓔珞聽見他的聲音,忽然兔子似的從床上竄起,一臉抱怨:「葉大夫,能不能不要加黃連,太苦了!」
「這可由不得我,是上頭的安排。」葉天士用手指了指天,暗示這是來自天子的強製命令,之後開啟藥箱,從裡頭翻出一隻小藥瓶來,「硫磺膏是治療疥瘡的,不對癥,換這個吧!」
頓了頓,又試探地問:「瓔珞姑娘,我有事兒不明白……」
魏瓔珞雙手接過:「你問。」
「明知自己從小就對花生過敏,為何要故意服用,引發大片紅疹呢?而且,還找我偽造疥瘡的醫案……」葉天士問道,想起弘曆的所作所為,心裡有了一個答案。
這沒什麼不好回答的,又或者說最好給他答案,免得他自己胡思想。
「……我故意激怒皇上,他醒過神來,第一個就會找我算賬,可我若是染病,他就算氣得七竅生煙,也不好再罰我啦。」魏瓔珞微微一笑,麵帶著病態的蒼白,「畢竟誰都知道,我照顧皇上才會染病啊。」
Advertisement
葉天士略意外,仔細一想,又覺得一切合合理,當下佩服的點頭:「姑娘聰慧忠義,旁人難以企及一二,放心,草民一定儘力掩護,不會讓你出半點破綻!」
魏瓔珞笑而不語。
等到葉天士離開,才喃喃自語道:「忠義?我不過是藉機發泄心裡的怒氣罷了,誰他這樣對皇後娘娘……」
如蓮花開於淤泥中,皇後的品與宮中其他人相比,簡直可以算得上是纖塵不染。魏瓔珞很喜歡,有時候甚至會忍不住將與自己的姐姐作比較,然後得出結論……這兩人很像,無論是品格,還是溫照顧時的模樣……
魏瓔珞能為了姐姐隻宮,也能為了皇後怒罵弘曆。
「隻是罵人一時爽,接下來的日子不好過咯……」輕嘆一聲,卻並不後悔,旁沒人伺候,也不敢讓人伺候,拔開瓶蓋,勾了些藥膏在手上,艱難的為自己上好葯,然後便吹燭睡下了。
疼痛難耐,魏瓔珞難的翻了個,那些自己的手夠不著的地方,沒有上藥的地方,又又疼。
……是誰?
魏瓔珞沒有睜開眼,繼續閉著眼睛裝睡。
一隻冰涼涼的手落在的額頭上,靜靜試探額頭的溫度,良久才離。
之後,是拔開瓶蓋的聲音,那隻手重新落回上,帶著藥膏的清香,作又輕又緩,胳膊後側,脖頸,後肩……那些自己夠不著的地方,他一一為上藥,卻又沒有越軌半步,後背後腰,這些男人不該的地方,他都沒有藉機去,哪怕此刻「睡著」,哪怕就算醒著也不會責怪他。
是的,這是一隻男人的手。
一個認識的男人的手。
瓶蓋重又蓋上,屋子裡寂靜下來。
魏瓔珞仍閉著眼睛,上舒坦了許多,心裡卻又又麻,不知自己此刻應不應該睜開眼,不知道自己該不該看一看他,然後對他笑一笑。
Advertisement
又怕他如往常一樣,落荒而逃。
直至一個溫的吻落在的睫上,如蜻蜓點水,如猛虎嗅薔薇。
魏瓔珞極力剋製,才能讓自己的睫不至於如自己的心一樣,方寸大微微抖。
直至關門的聲音輕輕響起,才睜開眼,嘆了口氣,抬手捂住自己被吻過的那邊睫。
「……這場病。」漆黑的夜裡,魏瓔珞不由得翹起角,「也不全是壞事。」
病來如山倒,病去如,葉天士的湯藥熬到第十日,侍衛所裡,傅恆正翻看著手裡一卷兵書,一雙手忽然從他後出,矇住他的眼睛。
「瓔珞,你怎麼來了?」傅恆任由矇住自己的眼睛,輕易的猜出了對方的份,笑著問,「你的病大好了?」
「你怎知是我?」魏瓔珞放下手,繞到他側,前幾日的病痛似乎讓消瘦了一些,愈發顯得楚腰纖細,不堪一握。臉上的笑意卻人了許多,對他的笑,總是與對別人的笑不同,「我大好了,多虧某個田螺公子心照顧我,每晚都為我更換額頭的帕子,用冷水手和手臂。」
「咳。」聽到田螺公子這個稱呼,傅恆不自然的以拳掩,咳嗽了一聲,「這人是誰呀?」
見他裝傻,魏瓔珞索跟他一塊裝傻,麵驚訝道:「不是你嗎?」
傅恆搖了搖頭。
「……那可怎麼辦?」魏瓔珞咬了咬,雪白貝齒在紅上留下幾道淺淺白印,「我以為他是你,才許他為我上藥,那些地方,我是不允許其他人男人的……」
傅恆聞言一愣。
「既然不是你,那我就走了。」魏瓔珞輕輕一嘆,轉離去。
「等等!」傅恆再也坐不住,起拉住的胳膊。
「……你還有什麼事要對我說?」別過臉不看他。
「我……」傅恆一時之間竟不知該與說什麼。
真是自作自,何苦要撒那樣的謊,如今要如何下臺?
「傅恆!」正在傅恆苦惱之際,好友的大嗓門門而,「連熬十天,我快散架了——」
哐當一聲,大門開啟,海蘭察保持著推門的作,愣在門口,眼珠子左右移了一下,訕笑道:「我是不是打擾到你們了?我這就走,這就走,你們繼續,你們繼續哈……」
「……十天?」魏瓔珞忽然回在傅恆口捶了一拳,麵頰如同的一樣殷紅,與其說是憤怒,倒更像是害,咬著牙道,「還說不是你!」
傅恆著奪門而去的背影,忍不住提手,他覺得自己也生病了,這個地方又又,像泡在溫湯中,像沐浴在花海中。
「我真不是故意的。」海蘭察見魏瓔珞跑了,以為是自己的錯,了手,小心翼翼的討好,「要不……我再替你值一天班?」
傅恆一拳砸在他口,他這一拳頭可不像魏瓔珞的花拳繡,裂石般的力道差點把海蘭察給捶吐了。
「不需要!」傅恆笑道,「你這個大!」
他的心如有花開,層層疊疊,相比之下,另外一個人的心就不那麼麗了。
「你說什麼?」
養心殿中,又碎了一隻茶盞。
弘曆麵難看地坐在床沿:「你說那個賤婢已經回長春宮了?什麼時候?不是還病著嗎?」
「回皇上,魏姑娘已經痊癒,昨夜就已經搬回長春宮了。」李玉小心翼翼的回道。
弘曆一聽,怒不可遏,隨手打翻了旁的銅盆,銅盆滾落,溫水落了一地,殿中的人也跪了一地。
「明明在朕之後染病,病程最一個月!」弘曆冷冷道,「為何還能比朕先痊癒?」
「這……這……」李玉吞吞吐吐道,「也許……病得輕一些?」
「因為從頭到尾都沒病!」弘曆怒道,「把這個賤婢找來,這一次朕一定要親手剝了的皮!」
「皇上怎麼了?發這樣大的脾氣。」一個溫平和的聲音忽然響起,眾人循聲去,都在對方的笑容中定下神來。
世上隻有兩個人,笑容有此安定人心的力量,一個是觀音,還一個是皇後。
即便是弘曆,看見的笑容,怒氣也去了一半,正待將剩下的一半怒氣發泄出來,忽聽道:「臣妾一路走來,聽見不宮人在誇皇上呢。」
「哦?」弘曆略意外,「他們都說了些什麼?」
「很多。」皇後在床沿坐下,「譬如皇上能忍常人不能忍,魏瓔珞為治病冒犯了您,您卻毫不計較,是個寬宏大量的明君。」
弘曆一聽,麵古怪。
「不但不怪,在知道被您染了惡疾之後,沒有趕離開,反而許留在養心殿,讓最好的大夫給看病,實乃有德之君,千古難尋……」皇後繼續道。
「夠了!」弘曆再也聽不下去,開口打斷。
皇後便不再開口,隻笑地看著他。
李玉小心翼翼打量他二人的臉,見兩人都不開口,隻好自己開口道:「皇上,那魏瓔珞……還要不要拿回來?」
弘曆不好對皇後發火,見他撞自己槍口上,立即掉轉槍頭,將火撒在他上,龍靴蹬在李玉口,一下子將他踹翻,弘曆怒氣沖沖道:「你沒聽見嗎!人家出言激怒,是為了救朕!染惡疾,是為侍疾!就算傳揚出去,人人贊是不畏強權的忠僕!更何況,病都痊癒了,再也抓不住痛腳!朕若現在降罪,豈非了不識好歹的昏君!朕這纔是啞吃黃連,有苦說不出!」
說著說著,他臉真出一苦,彷彿接二連三地吃了黃連、木通、龍膽草,苦參……
那些他灌在魏瓔珞碗裡的葯,如今全吃在了他自己裡。
真苦,苦不堪言。
猜你喜歡
-
完結711 章

惜花芷
藏拙十五年,花芷原以為自己可以做一個最合格的世家千金安穩一輩子,可當花家大廈將傾,她不得不展露鋒芒出麵撐起這個風雨飄搖的家,拋頭露臉是常態,打馬飛奔也常有,過不去了甚至帶著弟妹背著棺材以絕戶相逼,不好惹的名聲傳遍京城,她做好了家族一朝反目戳她刀子的心理建設,也做好了孤獨終老的準備,獨獨沒想到會有人在出征前盔甲著身向她許終身!好稀奇,這世上竟然還有人敢娶她!?
132.4萬字8 211843 -
連載715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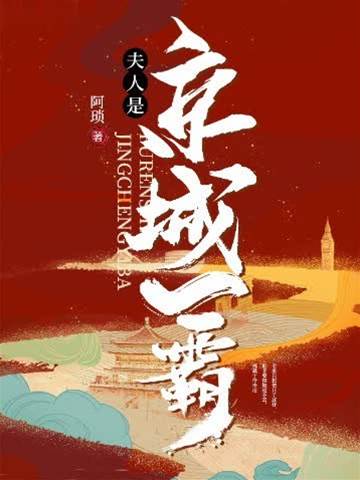
夫人是京城一霸
七姜只想把日子過好,誰非要和她過不去,那就十倍奉還…
120.8萬字8 12111 -
完結201 章

逆天嬌妃:皇上把持不住
宋微景來自二十一世紀,一個偶然的機會,她來到一個在歷史上完全不存在的時代。穿越到丞相府的嫡女身上,可是司徒景的一縷余魂猶在。
52.1萬字8 27669 -
完結123 章

我不做妾
沈瀾穿成了揚州瘦馬。 雲鬢花顏,瑰逸絕倫,當得起江南第一美人之稱。 正因這份美貌,她要被送去給巡鹽御史裴慎做妾。 沈瀾不願意做妾,千辛萬苦逃了出去。 陰錯陽差,成了裴慎的丫鬟。 對丫鬟這份工作,沈瀾尚算滿意。 雖然全年無休007,但薪俸極高,常有外快。 更讓她滿意的是裴慎快要成親了。 只等裴慎成婚後,她便能銷去奴籍,靠着自己積攢的人脈、錢財,快快樂樂過完這輩子。 就在她滿心歡喜,只等放良之時,忽然發現,裴慎想納她爲妾。 沈瀾:我不做妾。 * 裴慎三年前就想納沈瀾爲妾,只是因爲守孝不得已忍了三年。 越隱忍,越剋制,想得到她的心思就越強烈。 如今三年已過,將要成親,正是納妾的好時候。 * 裴慎一生順風順水,官路亨通,遇到沈瀾,才知道世間唯情愛二字,最是摧心折肝。
39.9萬字8 74912 -
完結206 章

賠罪
施綿九歲那年,小疊池來了個桀驁不馴的少年,第一次碰面就把她的救命藥打翻了。 爲了賠罪,少年成了施綿的跟班,做牛做馬。 一賠六年,兩人成了親。 施綿在小疊池養病到十六歲,時值宮中皇子選妃,被接回了家。 中秋宮宴,施綿跟在最後面,低着頭努力做個最不起眼的姑娘,可偏偏有人朝她撞了過來,扯掉了她腰間的白玉銀環禁步。 祖母面色大變,推着她跪下賠禮。 施綿踉蹌了一下,被人扶住,頭頂有人道:“你這小姑娘,怎麼弱不禁風的?” 施綿愕然,這聲音,怎麼這樣像那個與她拜堂第二日就不見蹤影的夫婿?
33.9萬字8.18 4111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