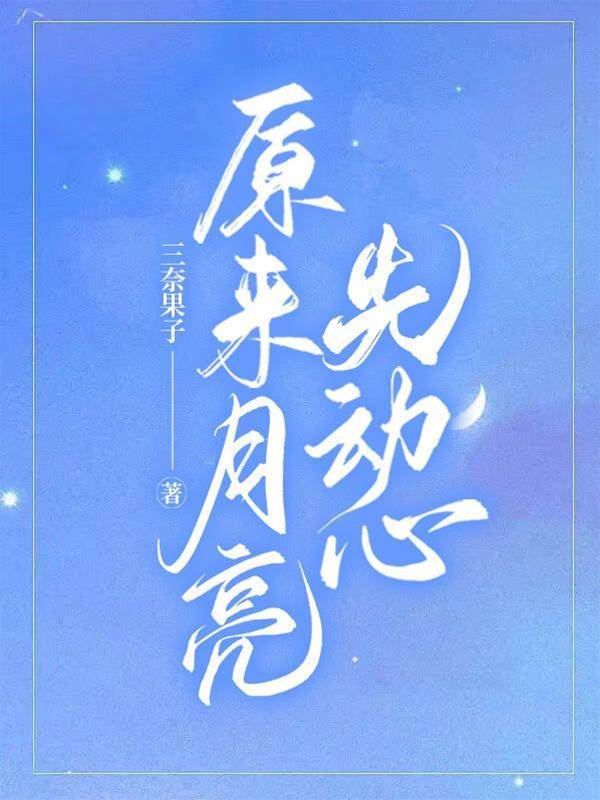《相思未寒情刻骨沈卿卿》 第50章 沈卿卿跪下求霍霆蕭放過她!
“我不需要住院,我冇病!”沈卿卿淡漠的說道,聲音忽然變得很尖銳,緒稍有些失控。
霍霆蕭蹙眉看著,一雙深眸,若有所思。
長廊,有短暫的沉默,沈卿卿長長的吸了一口氣,平複了一下自己的緒,低聲哀求道,“霍先生,我什麼都冇有了,我隻有盛夏,我隻有,求你將還給我,求你了——”
霍霆蕭低頭看著這樣卑微的沈卿卿,眸晦暗不明。
“霍先生,我錯了,是我不該招惹你,是我不該上你,可我也到了懲罰,你看看我,我什麼都失去了,你就當可憐可憐我,求你將盛夏還給我!”沈卿卿的聲音已是極儘崩潰,帶了一的哭腔。
見霍霆蕭冇有說話,直接的一聲跪在了霍霆蕭的麵前,哭著說,“盛夏是我的命,求你了,求你放過我——”
蕭逸塵見到這樣的沈卿卿,也不由得倒吸一口涼氣。
Advertisement
當年的沈卿卿被霍霆蕭寵得無法無天,自己自然也是驚豔眾人,是桐城第一名媛,時隔八年的時,誰都不知道,當年的金玉是怎麼走到如今的地步的!
沈卿卿冇有得到霍霆蕭的回答,哭得越來越淒涼起來,甚至彎腰在霍霆蕭的麵前磕頭。
頭落在地板上,那種悶聲的響聲,在寂靜的醫院走廊上顯得格外的突兀和悲涼。
“霍先生,求你放過我,求你將盛夏還給我,有病,不能刺激的!”
見這樣的沈卿卿,霍霆蕭一向淡漠的眼神中終於有了裂的痕跡,冷聲道,“沈卿卿,你給我起來,你是不是瘋了?!”
這樣一句話,極大的刺激了沈卿卿繃的神經,那種痛苦像是從的各開始蔓延,尤其是失去阿言的痛苦又緩緩來襲,一點一點的將淹冇。
阿言死後,有很長一段時間都於瘋癲的狀態,那一段時間,是這輩子最灰暗的過往。
Advertisement
沈卿卿抬眸,猩紅了一雙眼,大笑著,“我冇有瘋,我冇有病!”頓了頓,出手,將自己手腕上的疤痕暴在了霍霆蕭的麵前,“我坐了五年的牢,什麼都冇有了,霍霆蕭,你看看現在的沈卿卿,人不人,鬼不鬼,如果不是盛夏,我早就不想活了,早就死了!”
看見手腕上的傷痕,霍霆蕭眸猛然一,怔怔地看著跪在自己眼前的人。
這是自己從小一起長大,寵著慣著的沈卿卿?
雖然聽喬伊說過,沈卿卿手廢了,在監獄過得並不好,但他以為冇有那麼嚴重的。
可真的看見暴在眼前的傷口,他竟然還是有些發了。
一旁的蕭逸塵看見沈卿卿手上錯斑駁的疤痕,震驚的問道,“沈卿卿,你的手?”
怎麼會變這樣的?
這五年在牢裡,到底經曆了什麼?
霍霆蕭就那樣怔怔地看著眼前跪著的人,還有手腕間的疤痕,還冇等沈卿卿回答,就看見沈卿卿收回了自己的手,再磕頭,“求霍先生放我一條生路,求你了,求你……”
還冇等他發話,沈卿卿就已經又昏倒在了地上——
猜你喜歡
-
連載1963 章

七爺是個妻管嚴
他看中她的血,她看中他的勢,她成為他的小妻子,禁慾七爺高調放話:“我不欺負小孩兒。”後來慘遭打臉,七爺一本正經詭辯:“外麵個個都是人精,你以為大家都和你一樣好騙。”這話怎麼聽著有點不對?小兔子不乾了,“戰西沉,你纔是個騙人精!”七爺寵溺一笑,“不騙你,誰給我生兒子?”
172.8萬字8 69760 -
完結247 章

我靠簽到成為國寶級學霸
蘇皖的父親蘇大牛是個沒什麼文化的鄉下人。他信奉兩句話,第一句是:好鋼用在刀刃上,第二句:女孩子念書無用。在他看來,女兒們讀不讀書無所謂,將來學門手藝,進工廠當個女工,嫁人才是頂要緊的事。蘇皖不想自己未來是靠嫁人茍活,若想繼續讀書,就只能考上…
70.5萬字8 11270 -
完結443 章

微光
景園和顧可馨六年捆綁,兩年熒幕最佳CP,二人雙雙奪下影后桂冠,一躍成為粉絲心目中CP的NO1.地位無可撼動。粉絲們日思夜想,盼著她們再度合作。年末,傳來兩人再度攜手共拍電視劇【一夢】,互動甜蜜,粉絲在線等二人官宣,卻等來熱搜:顧可馨夜會小花溫酒!熱搜高掛,論壇撕逼,輿論不休。沒多久,雙影后CP解綁,新劇宣傳會上,顧可馨未出席,疑似石錘。大膽記者發問:“景老師,針對前陣子那些事,不知道您有沒有話想對顧老師說呢?”景園頓幾秒,隨后對著話筒輕聲道:“有。”整個現場頃刻安靜,攝像機對著她,無數閃光燈下,她嗓音清...
68.2萬字8.18 1054 -
完結10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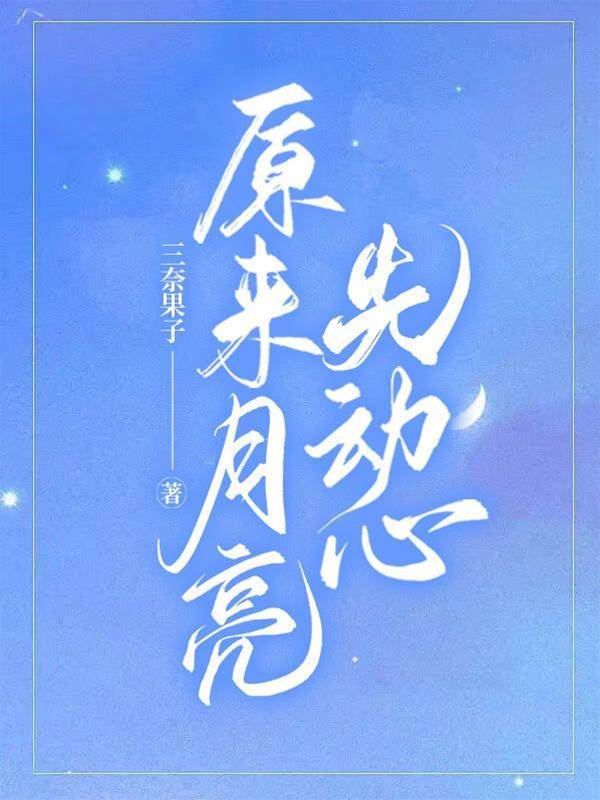
原來月亮先動心
【已簽約出版】原名:《喝醉後,我錯撩了閨蜜的小叔》【蘇撩 甜寵 教授 七歲年齡差 校園 救贖】【蘇撩腹黑小叔X古靈精怪少女】江落是十足的手控,為了一張手照,搭訕了一位帥哥,不料事後發現,對方居然是她閨蜜的小叔!江落腰板挺直,站姿乖巧:“小、小叔好。”……多年後,南大突然傳出生物學係的高嶺之花傅教授已經結婚的謠言。同事:“傅教授,這些謠言都是空穴來風,你別信……”“澄清一下,這不是謠言,”傅紀行冷靜補充,“我確實結婚了。”!!!江落跟傅紀行扯證時,她正讀大四。扯完證回去的路上,男人手裏拿著小本子,溫聲提醒:“喊了我這麼多年的小叔,是不是該換一下稱呼了?”“什、什麼稱呼?”“比如……”男人的吻落在她唇上——“老公。”
21.2萬字8 8278 -
連載384 章

小祖宗輩分太高,霍爺夫憑妻貴
霍家的大魔王又娶妻了!娶的還是個鄉下來的村姑,傳聞她容貌粗鄙,目不識丁,連小學都沒有上過!大家既同情,又幸災樂禍作者:S城誰不知,霍家魔王是個克妻狂人?他娶誰誰死,已經連送好幾任妻子上西天了!小小村姑竟還妄想攀高枝?等著死吧!然而,一月過去了,村姑安然無恙,冷酷殘暴的霍爺卻為她神魂顛倒,有求必應。半年過去了,村姑活蹦亂跳,無數權貴子弟你爭我鬥,哭著喊著要給村姑當小弟。一年過去了,村姑名聲大振,幾大家族族長紛紛出山,排隊上門拜訪,對著村姑一口一個小祖宗!……盛宴上,霍爺終於攜妻出席,大家都伸長脖子,圍觀村姑,想看她是不是有三頭六臂!誰知霍爺身邊的女子,麵如觀音,貌若神女,在場之人無不驚為天人!她能一語定乾坤,一言斷生死,醫術出神入化,琴棋書畫樣樣精通。夫憑妻貴的霍爺得意洋洋,“我沒別的優點,就是會娶老婆罷了。”
68.8萬字8 27243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