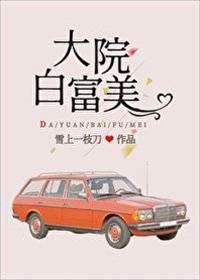《禁愛合歡》 第一百十五章 懷孕風波2
5 懷孕風波2
沉重的眼簾驀然瞠大,安以默難以置信地看著眼前的男人,勉力從床上撐坐起來:“你,說什麼?”
殷煌神越發沉,不帶任何轉圜,依舊給出三個相同的字:“打掉他!”
“為什麼?”安以默大打擊,撐著床沿的手臂抖不已。沒有想到殷煌竟然冷到連自己的親生骨都不要。
殷煌薄抿,冷狠絕的目落在安以默臉上,忽然手重重住下咬牙切齒:“你還有臉問我為什麼?我是不是對你太好了才讓你以為可以這樣踐踏我的尊嚴,踐踏我對你的?不,你這種人盡可夫的人本不配談!”
下被得生疼,殷煌手勁打得幾乎要把的骨頭碎,可是他殘冷的話卻讓安以默茫然起來。
“人盡可夫?”下制,連說出來的話都含糊不清,可的目卻異常清澈,不閃不避看著他質問“你憑什麼這麼說我?你把話說清楚!”
殷煌一臉嫌惡,一把甩開對的牽制,似乎連一下都嫌髒:“別用那種眼神看我,你讓我覺得髒,覺得惡心!如果你乖乖把孩子拿掉,也許我還有可能放你一馬,不然我會讓你跟你的夫一起下地獄!”
安以默越聽越抓狂,幾乎快分不清究竟是瘋了還是殷煌瘋了,為什麼他說的每一個字都聽不懂?
“你在說什麼?什麼我和我的夫?我的男人除了你還有別人嗎?”大聲吼。
冷眸一瞇,薄輕勾,殷煌冷笑著居高臨下看,就像看著一塊骯髒不堪的抹布:“還要狡辯?也許你還不知道,早在一年多前我就做了結紮,我本不可能讓人懷孕,試問你的孩子從哪裡來的?”
Advertisement
結紮——一年多前?也就是……流產之後,他竟跑去結紮了!原來,當初傷害的並不止一人,他也同樣備煎熬,痛苦不堪!才會在出院之後避而不見,才會不聲不響跑去結紮,他當時的恐懼,痛苦,自責,懊悔又有誰知道呢?而卻一味沉浸在自己的巨大哀慟中難以自拔,完全將他的剔除在外。這對他又何其公平呢?
淚就這樣不聲不響地滾落。
他的一句結紮,牽扯出安以默多緒,悲傷,痛苦,悔恨……當初,他們都太執著,忘了對彼此留有餘地,那麼現在呢?殷煌依然是那個殷煌,無論失憶前還是失憶後都無可避免地上。
他,寵,溺,卻也霸占,控制,恨不得將與世隔絕起來。這是他的子,從來就是這樣不曾改變過,早就知道,上這個格極端又敏的男人將是萬分辛苦的,但既然決定了,就決不允許兩人之間存在任何障礙。
“怎麼不說話了?沒想到如意算盤落空了吧!你的野種算不到我頭上了,很憾吧!”殷煌冷笑,安以默流著淚痛苦悲傷的模樣就像一把鋒利的匕首一下一下在他心窩上剜,一刀刀,鮮淋漓,千瘡百孔。如果他夠心狠,他恨不得殺了,可是他下不了手,即便這樣他也做不到傷害,那是他掏心掏肺著的人,是他的命,可是現在卻在要他的命!
高大的形微微晃了晃,殷煌竟覺得有些站不住,閉了閉眼,穩住形,耳邊卻傳來安以默鎮定平靜的聲音:“送我去醫院吧!”
殷煌睜眼看,目中閃過一不確定:“你願意打掉孩子了?”
Advertisement
安以默深吸一口氣,淡淡道:“至應該去做個檢查不是嗎?”
深夜,婦科只有一名值班醫師。安以默依舊發著高燒,坐在醫院整潔舒適的走廊裡等報告,殷煌眼神冰冷站一邊,任燒得滿臉通紅,虛弱地靠在椅背上。
十分鐘後,檢查報告出來,尿報告顯示沒有懷孕。
安以默沒有去拿報告,早就知道會是這樣的結果,本連看一眼都懶得,現在的腦子昏昏沉沉的,只想睡覺。
殷煌抓著報告看了許久才將目移至幾乎昏睡過去的人上,拿著報告的手微微抖,半晌才蹦出一句:“沒有懷孕!”
意識逐漸模糊的子閉著眼睛點點頭,含糊不清地咕噥:“我知道,你告訴我結紮之後我就知道會這樣,之前可能是上的一些狀況讓我誤會了吧!好困,別煩我!”說著再也支撐不住,子慢慢往邊上歪去。
耳邊只剩男人驚駭的吼聲:“安以默——”
淡淡的花香從窗外飄進來,馥鬱芬芳;歡快的鳥鳴從枝頭傳來,清脆悅耳。好的清晨總是令人向往。安以默從沉睡中醒來,仰頭就看到潔白的廣玉蘭掩映在綠葉之間,陣陣香氣就是從那一朵朵碩大的花朵當中散發出來的,而花與葉之間,一只畫眉躲在枝頭唱得歡,無憂無慮的樣子人羨慕。
手上傳來的熱意牽引的目,床沿上一顆大大的腦袋靠著的手臂,一只大掌牢牢握著的小手,不放。
這個傻瓜,守了一夜吧,也不知道睡到邊上的沙發上去,總好過趴在床邊睡一夜,一會兒鐵定要喊脖子痛了。不過最可惜的還是昨晚沒撐得住睡過去了,想必錯過了許多彩片段。殷煌看到那張檢查報告不知道會是什麼表,吃驚?高興?懊惱?自責?還是覺得被耍了?
Advertisement
哎——希不是最後一種。真心不是要耍他,昨天那種況再多解釋也沒用,他那多疑又極端的子只有帶他一起來醫院,讓事實來證明,他才會真正相信,放心。
“老公……”推推他。
稍稍一,殷煌就醒了,驚跳著坐起來,見安以默睜著眼睛看他,連忙俯到面前:“你要什麼?哪裡不舒服?”
安以默皺皺眉,弱弱地開口:“哪裡都不舒服!”
殷煌輕輕著的發,聲安:“你高燒剛退,現在還很虛弱。不過醫生說沒事的,就是前一陣子太累了,又有些腸胃功能紊造的連鎖反應,休息幾天就好了。”
說著,殷煌倒了一杯水了支吸管遞到邊:“來,喝點水!”
默默喝完一杯水,兩個人頓時陷沉默。
殷煌不說話,安以默也不開口打破沉默,甚至故意別過頭去不看他。
許久,才聽到他輕輕歎了口氣:“寶貝,別生我氣。”
他一出聲,安以默就來勁了,一撇,眼一瞪:“不生你氣生誰氣?這麼大的事你也不告訴我,你是想一輩子瞞著我,以此來不斷試探我,測試我對你的忠貞嗎?姓殷的,你是不是太過分了?”
殷煌急得連連搖頭:“不是這樣的,你聽我解釋!”
“不聽不聽!”故意捂住耳朵,“你不聽我解釋,我也不聽你解釋!昨晚你讓我百口莫辯,現在你又想補救了,沒門兒!”
殷煌抓狂地爬爬頭發,抓下捂住耳朵的兩只手,大聲道:“你必須聽我說!”
靜下來,委屈地撇撇,忽然就哇的一聲哭出來。
Advertisement
“壞蛋,土匪,惡霸,你還敢兇我,嗚嗚嗚——你走開,走開!”
殷煌頓時慌了手腳,一把抱住,附在耳邊不斷低聲下氣認錯討饒:“對不起,寶貝對不起,我不是故意要兇你,你不肯聽我解釋我才大聲的。”
“嗚嗚——你還怪我,還怪我!嗚——你討厭,既然是我不對你走好了,我不要再見你了,你走呀!”一邊哭一邊拿腳蹬他。
他抱著,又是一迭連聲地賠不是:“是我不對,都是我不對我不好!我不該怪你,不該兇你,老公錯了,你別生氣,病才剛好,氣壞子我心疼!”殷煌此刻是一點脾氣都沒有了,一的冷漠傲骨都被懷裡的小人磨了個,哪裡還有半點盛天董事長叱吒風雲,指點江山的氣勢?
偏偏懷裡的小人不領,一直哭一直哭,哭累了才漸漸在他懷裡平靜下來,鼻子一吸一吸,淚痕未幹。
殷煌幹脆了鞋上床來,從後面抱著,一手探擺,過細膩平坦的小腹,緩緩上移至線以下,然後溫的握上一方綿。
“寶貝,我你,你要相信我這輩子只會你一個。”他把頭埋頸間輕嗅。
安以默歎口氣,有些悲哀地說:“你要我相信你,那你呢?你又相信我多?每次出了事,你總是第一個質疑我,讓我百口莫辯。我真的好怕,萬一哪一天,又發生了什麼事,我解釋不清,也拿不出證據來證明要怎麼辦?殷煌,我不會每次都能那麼幸運跟你解除誤會的,我好怕,真的好怕!一次次被懷疑,一次次從你眼裡看到深切的厭惡和不信任,我怕有一天,不是你厭棄了我,就是我厭煩了這樣無休止的回。我不想看到彼此在痛恨中越走越遠,當哀莫大於心死的時候,才發現我們的竟然是那樣不堪一擊。”
的話在殷煌心裡引起深深的震。的確,他要求全心依賴信任,那他給予的信任又有多呢?說得對,每次一出事,他首先就質疑,為什麼?是得太深沉容不得一粒沙子,還是他從心底裡就防備著每個人,包括自己深的人?
的要求很簡單,只要信任而已,可的要求又太難,在他的世界裡從來就沒有“信任”二字,凡事都看證據,看結果,他想要知道的事從不聽別人說,只靠自己查,眼見為實。他有強大的意志,任何事都有自己的判斷和自一套的事方式,不偏聽偏信,這使他在商場上無往不利,戰無不勝。
可是這東西不是一加一等於二這麼簡單,也不是單憑理智就能解決問題,如果夠理智也不會深深上了。
在他要求的信任時也能要求他。既然要求,他便試著去信任,試著毫無原則的,盲目地去相信自己深的人,也許也是一種幸福。
安以默住院這段時間,sece的營業狀況卻非常良好,每天的營業額都在二十萬以上,比的預期超出很多。
出院後,就馬不停蹄去視察店面了,殷煌攔不住,又擔心吃不消,只能推了工作陪一起。
兩人雙雙出現在店裡更是引來狂熱追捧,一時間,兩人一起工作,一起吃飯,一起視察的照片被各大網絡紛紛轉載,一組組甜恩的合照了網絡上點擊率極高的鏡頭。
sece這一品牌,更是名噪一時,竟了時尚的代名詞。
事業上的如日中天卻並未給安以默帶來多大的快,自從知道殷煌結紮,不知道催過他幾次去做複原手,可殷煌只是點頭漫不經心應著,並沒有任何實際行。
再催,殷煌就幹脆把在下狠狠上幾遍,完了還氣定神閑地問:“要不要再戰幾個回合?”
被他折騰得只剩半條命,出氣多,氣,聞言驚懼地搖頭:“不要了……再來會死人的!”
於是殷煌薄一勾,給出結論:“瞧,做不做手完全不影響夫妻生活的和諧,何必多此一舉?”
著氣反駁:“可是……”
“可是什麼?你不贊同?那再來!”
於是,只剩半條命的人又被按著猛幹數回,沒等男人盡興釋放便徹底昏厥。
殷煌不去做複原手絕不是工作太忙沒時間,也絕不是他為了證明自己某些方面的能力天賦異稟。安以默覺得出,他只是在不斷地回避這件事,甚至只要稍稍提起一點,就開始不耐煩,或者直接撲倒,在床上武力解決,暴力鎮,讓一句話也說不出。
是什麼原因讓殷煌如此回避?他不想安以默懷孕已是不爭的事實。是不願懷他的孩子嗎?安以默立即搖頭否決。殷煌的深絕不是作假,他是真,可以說骨。更何況,殷煌除了本不會跟別的人上床。那麼,唯一的可能就是他不想要孩子,非常不想。
猜你喜歡
-
完結88 章

和周先生先婚後愛
婚後,宋顏初被周先生寵上了天。 她覺得很奇怪,夜裡逼問周先生,“為什麼要和我結婚,對我這麼好?” 周先生食饜了,圈著她的腰肢,眼眸含笑,“周太太,分明是你說的。” 什麼是她說的?? —— 七年前,畢業晚會上,宋顏初喝得酩酊大醉,堵住了走廊上的周郝。 周郝看著她,隻聽她醉醺醺地歪頭道:“七年後,你要是還喜歡我,我就嫁給你吧!” 少年明知醉話不算數,但他還是拿出手機,溫聲誘哄,“宋顏初,你說什麼,我冇聽清。” 小姑娘蹙著眉,音量放大,“我說!周郝,如果七年後你還喜歡我,我就嫁給你!”
13.1萬字8.09 58565 -
完結280 章

總裁夫人她馬甲轟動全城了
前世,花堇一被矇騙多年,一身精湛的醫術被埋冇,像小醜一樣活了十三年,臨死之前她才知道所有的一切不過是場巨大陰謀。重生後,她借病唯由獨自回到老家生活,實則是踏入醫學界,靠一雙手、一身醫術救了不少人。三年後她王者歸來,絕地成神!先替自己報仇雪恨,嚴懲渣男惡女;同時憑藉最強大腦,多方麵發展自己的愛好,畫家、寫作、賭石...隻要她喜歡,她都去做!她披著馬甲在各個行業大放光芒!權勢滔天,富豪榜排名第一大總裁席北言:媳婦,看看我,求求了!餘生所有,夢想、榮耀、你。
51.6萬字8 29860 -
完結21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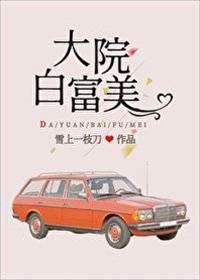
七零大院白富美
別名:大院白富美 肖姍是真正的天之驕女。 爸爸是少將,媽媽是院長,大哥是法官,二哥是醫生,姐姐是科學家。 可惜,任性的她在婚姻上吃了虧,還不止一次。 二十二歲時,她嫁給了識于少時的初戀,可惜對方是個不折不扣的渣男,兩年后離婚。 但她并沒為此氣餒,覺得結婚這事兒,一次就美滿的也不太多。 二十六歲再婚,一年後離婚。 三十二歲三婚,閃婚閃離。 功夫不負有心人,在集齊了極品婆婆,極品小姑子,極品公公之後,她終於遇上了最適合的人。 三十五歲肖姍四婚,嫁給了最後一任丈夫趙明山,二人一見鍾情,琴瑟和鳴,恩愛一秀就是幾十年。 重生後,她麻溜的繞過一,二,三任前夫,直接走到趙明山的面前,用熱辣辣的目光看著他, “哎,你什麼時候娶我啊?” 趙明山一愣,肩上的貨箱差點砸到腳了。
97萬字8 12440 -
完結1436 章

我在娛樂圈修仙
【女強+絕寵+修仙】暴發戶之女林芮,從小到大欺女霸男,無惡不作。最後出了意外,一縷異世香魂在這個身體裡麵甦醒了過來。最強女仙林芮看了看鏡子裡麵畫著煙燻妝,染著五顏六色頭髮的模樣,嘴角抽了抽。這……什麼玩意兒?! “雲先生,林影後的威亞斷了,就剩下一根,她還在上麵飛!” “冇事。”雲澤語氣自豪。 “雲先生,林影後去原始森林參加真人秀,竟然帶回來一群野獸!” “隨她。”雲澤語氣寵溺。 “雲先生,林影後的緋聞上熱搜了,據說林影後跟一個神秘男人……咦,雲先生呢?” (推薦酒哥火文《我,異能女主,超兇的》)
135.2萬字8 23125 -
完結169 章

勾月亮
『特警隊長×新聞記者』久別重逢,夏唯躲著前男友走。對他的形容詞隻有渣男,花心,頂著一張帥掉渣的臉招搖撞騙。夏唯說:“我已經不喜歡你了。”江焱回她:“沒關係,玩我也行。”沒人知道,多少個熬夜的晚上,他腦海裏全是夏唯的模樣,在分開的兩年裏,他在腦海裏已經有千萬種和她重逢的場麵。認識他們的都知道,江焱隻會給夏唯低頭。小劇場:?懷城大學邀請分校特警學院的江焱學長來校講話。江焱把她抵在第一次見她的籃球場觀眾席上撕咬耳垂。他站在臺上講話結束後,有學弟學妹想要八卦他的感情生活,江焱充滿寵溺的眼神落在觀眾席的某個座位上。一身西裝加上他令人發指的魅力,看向觀眾席的一側,字音沉穩堅定:“給你們介紹一下,你們新聞係的19級係花小學姐,是我的江太太。”--婚後有天夏唯突然問他:“你第一次見我,除了想追我,還有沒有別的想法?”他低頭吻了吻女孩,聲音帶著啞:“還想娶你。”他擁抱住了世間唯一的月亮......於是恨不得向全世界宣布他江焱——已婚!〖小甜餅?破鏡重圓?治愈?雙潔〗
28.6萬字8 7527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