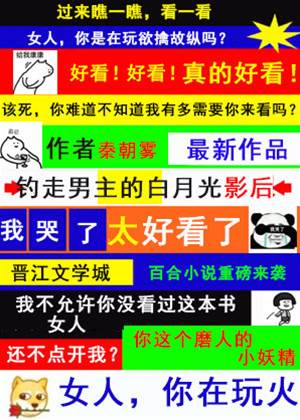《舊夢1913(出書版)》第六章 寧安府 1908,光緒三十四年,戊申 (1)
『孩子是你的。』
『我知道。如果不是我的,孩子又怎麼會死?如果是他的,你又怎麼會舍得讓孩子死?』
一直到傅蘭君病初愈,顧靈毓都沒有回家來。
再也不問顧靈毓的消息,只是一個人坐在床上靜靜發呆,桃枝看不過去,勸傅蘭君:“小姐,今天天氣不錯,出去散散步吧?”
衛兵自出事那日起就撤了崗,現在是自由的。
傅蘭君從愣怔里回過神來,“哦”一聲:“那就回娘家看看吧。”
桃枝面有難:“小姐你大病初愈,怕是不得馬車顛簸,再者老爺那邊也還病著。上次夫人走的時候悄悄跟我說,怕老爺擔心,您這邊的事還沒同老爺講呢。你如今這乍一回去,豈不穿了幫讓老爺著急,不如先跟夫人通通氣,讓慢慢地把事給老爺知道,咱們再回家。”
桃枝想得周到,傅蘭君點點頭,桃枝扶起來:“今天咱們就先去外面曬曬太看看花。”
桃枝攙著出了門,今天天氣果然很好,曬得人筋骨,傅蘭君輕輕掙開桃枝:“我還沒有虛弱到走不路的地步,我想自己逛逛,你先回去吧。”
桃枝一千個不放心,一步一回頭地離開。傅蘭君獨自一個人慢慢在園子里漫無目的地逛著。獨自一個人時思緒總是瘋長如蓬草,嫁顧家三年,顧家的每一寸土地都和顧靈毓牽著手逛了,一草一木皆有故事,讓聯想起從前,從前多好,山清水秀太高,花香草芳好風飄。這一叢玫瑰,顧靈毓剪下過一枝為簪在鬢角,那一片草地,曾和他在此休憩,那是嫁進顧家第二年的夏天,他們走累了在草地上席地而坐,小夫妻兩個講了好些甜甜的私房話,枕著他的膝蓋睡著了,醒過來時手指上有個草戒指,是他趁睡的當口隨地拔草編織的。
Advertisement
那編戒指的草邊緣是鋸齒狀的,劃破了他的手指,草戒指兜住一滴鮮紅的,悠悠的,像一顆鮮亮的紅寶石。
傅蘭君抬起手看著那曾經戴過草戒指的手指,草戒指早已不見了,記憶的塵埃里,回憶不起那草戒指的樣子,只記得那一滴,清晰如故又添新,讓心驚不已。
再往前走,痛楚攀上心頭,這涼亭,齊云山曾經在這里對推心置腹,給磕過一個響頭,求從此對他的阿秀好一些,而如今,那給磕頭的人正在巡衙門大牢里,等著秋后的決……
走到后花園盡頭,出了后花園就是廚房下人們的所在,傅蘭君剛要轉,卻被嘁嘁喳喳的討論聲所吸引,猶豫了一下,稍稍走近一些,藏在八角門前的樹下。
是一群老媽子聚在一起閑聊,下人們閑聊八卦,圍繞的當然是主子們,坐在中間的廚娘邱嬸神神地開口:“爺還沒回來?”
有人搭腔:“可不是麼,小產快十天了也不見爺面,我活了幾十年,還真沒見過這樣狠心的人,年夫妻有什麼話不能攤開了說?看兩個人平日里恩恩,爺溫的,沒想到竟然是這種人。”
邱嬸嗤笑一聲:“你懂什麼,爺自然有他的道理。”
低了聲音,故作神:“我聽說,咱們這位,懷的本就不是顧家的種!”
瞬間一石激起千層浪,其他人都一副難以置信的模樣:“這不可能吧,你可別胡說八道。”
眾人的反應讓邱嬸很是滿足,有竹似的分析:“怎麼不可能?若是別的大戶人家,眷大門不出二門不邁也不見外男,出這種事當然是不可能,但咱們這位又不是個安分人,天地往外跑,又是去聽戲又是辦學,一天里暗地里能見的男人多了去了。不說別的,你們知不知道那個剛被砍頭的黨南嘉木?外面都說,爺去抓南嘉木的那天晚上,就和南嘉木在一起!”
Advertisement
聽眾們倒吸一口涼氣,嘁嘁喳喳地吵鬧起來,邱嬸很滿意自己造的轟,繼續自己知道的“幕消息”:“不僅如此,聽說咱們和南嘉木還被撞見過一次同在戲園子里聽戲。是巡警撞見的,我有鄰居家的小子就在巡警隊里,這你們都知道的吧,這消息絕對假不了。”
這“一手資料”給的話平添了許多可信度,聽眾們紛紛附和:“說來是奇怪,嫁進來三年都沒什麼靜,怎麼偏偏姓南的一回來就有了?這事兒蹊蹺。”
最后,他們拍板定論:“難怪爺總不回來。被個黨戴了綠帽子,有家不能回,心里苦啊。這孩子沒了也好,要不然還要為個仇人養孩子,作孽哦。”
墻后樹下,傅蘭君聽得渾冰涼,萬萬沒有想到自己竟然會被人這樣惡意地揣度!
顧靈毓也是這樣想的嗎?如果不是,為什麼他遲遲不肯回家?
傅蘭君渾渾噩噩地往回走,原本和煦的突然間變得熾烈,太像是就懸在的頭頂,烘干了全部的,烤得頭暈氣促兩眼昏花。游魂似的走回到自己和顧靈毓的臥室前,桃枝正百無聊賴地蹲在地上玩樹枝,看到立刻站起來,桃枝的表有些奇怪,囁嚅著說:“小姐,姑爺回來了……”
臥室的門被從里面拉開,時隔兩個多月,那張悉的臉再次出現在傅蘭君面前。他比上次見面時更瘦了,瘦得全然失去了以往那個溫的富家公子的模樣,變了一個郁冷冽的軍人。
他的眼神在平坦的腹部過,他人瘦了形,以至于眼窩深陷,一雙漆黑的眼睛藏在眉骨的影下,看不出他的表是喜是悲。
Advertisement
驀地想起剛才聽到的話,傅蘭君惶恐起來,急促地口而出:“孩子是你的。”
顧靈毓面無表地著,了很久,他終于開口:“我知道。”
顧靈毓轉過去,聲音輕飄飄的,像于一個虛無的夢境:“如果不是我的,孩子又怎麼會死?如果是他的,你又怎麼會舍得讓孩子死?”
這話如一記耳重重地在傅蘭君的臉上,不可思議地睜大眼睛著他的背影。過了很久無聲地笑了,笑得淚流滿面,他竟然認為是故意殺死這個孩子的,僅僅因為他是這個孩子的父親。他認為在用殺死自己孩子的方式向他報復!
笑夠了,淚流盡了,緩緩開口:“顧靈毓,你放我走吧。”
顧靈毓霍地轉。著他的眼睛,傅蘭君重復:“你的罪孽,我已經替你償還了,你放我走吧。”
回答的,是簡短的幾個字,顧靈毓扔下一句短促的“你休想”,一陣風般地從邊掠過。
傅蘭君最終還是決定離開顧家回娘家,沒有告訴顧靈毓,專門挑了顧靈毓不在家的一天走。
沒想到的是,剛剛收拾好行李要上馬車的時候,顧靈毓回來了。
他騎著馬從軍營趕回來,趕路趕得急了,人和馬都氣吁吁滿臉淌汗,不等馬站穩他就從馬背上跳下來,一把抓住馬車的韁繩,表急慌慌的:“你不能走,我不許你走!”
傅蘭君靜靜地看著他,過了很久,平靜地說:“我父親生病了,我要回去照顧他。”
顧靈毓死盯著的眼睛,固執地不肯放手,傅蘭君繼續說:“我是嫁進了顧家,不是賣進顧家。我爹生病,作為他的獨,我理應回去照顧他。”
Advertisement
顧靈毓像一個絕的孩子,絞盡腦卻無計可施,去意已決不可轉圜,他最終只能心有不甘地松開手,傅蘭君踩著板凳扶著桃枝的手鉆進馬車車廂。車把式甩韁繩,那馬不不慢地踏出去,顧靈毓魔怔了似的跟上去,一車一人就這樣一前一后地慢慢走著,車廂的簾子突然被掀開,傅蘭君探出臉來,顧靈毓面喜,他上前一步,卻又被傅蘭君接下來的話釘死在地上。
傅蘭君看著他,輕輕說:“不要再追了,何苦呢?顧靈毓,我好后悔當初去追你,如果就讓你去了日本,或許你現在還在日本,手上也就不會有這些債。我好后悔,我們之間,每一次追逐都是錯誤,或許我們之間本來就是個錯誤。”
說完這席話,松開手,簾子垂落下來,將的面容遮蔽在后。
車把式突然揚起鞭子對著馬猛地一,馬吃痛,撒開四蹄狂奔,很快就消失在了長街的盡頭。顧靈毓站在原地,著馬車后揚起的塵埃,怔怔地了很久很久。
回到娘家,傅榮的病已經好得差不多,姨娘也早已經把傅蘭君小產的事給他知道了。
傅蘭君伺候傅榮吃藥,傅榮出手來挲著的鬢發:“丫頭,苦了你了,爹一心想給你找門好親事,沒想到到頭來還是這樣。”
傅蘭君垂著眼睛攪拌藥湯:“算得了運算不了命,不怪您。”
傅榮喃喃自語:“是啊,算得了運算不了命,這事兒是怪不了爹,可是又能怪誰呢?”
是啊,該怪誰呢?
傅榮吃完藥,乏了要睡覺,傅蘭君悄悄退出去,桃枝在外面沖招手:“小姐,來人了。”
來的人很讓傅蘭君意外,竟然是焦姣。
不是進京告狀去了嗎?懷著疑問傅蘭君來到臥房,焦姣就在那里等。
幾個月不見,憔悴了很多,原本明艷無匹的東北姑娘如今卻如萎謝的殘花,看上去神也不甚正常,整個人恍恍惚惚的。傅蘭君握住的手拉著坐下,的雙手很冷,渾如窖藏的冰。
傅蘭君拉著的手只是沉默,不知道該說些什麼。毫無疑問,焦姣這次北京之行徒勞無功。焦姣走的時候就知道,此行必定徒勞無功,大清朝每一寸土地上都有冤死的鬼魂,哪有那麼多正義得以張?
最終是焦姣先開口,眼神茫然:“我救不了他。”
傅蘭君不知道該如何安,只能攬著的肩膀輕輕拍打著,機械地轉過頭來,用幾乎沒有焦點的眼神著傅蘭君:“一回來我就去了顧家,顧家人跟我說你回娘家了,我就找來了。你離開得對,顧家人無無義遲早會遭報應的,你離開得對……”
反復念叨著“離開得對”,傅蘭君悄悄沖桃枝使了個眼,桃枝走上前來攙起焦姣:“阿姣姐你肯定了吧,我帶你去吃點東西。”
桃枝攙扶著焦姣走了出去,傅蘭君茫然地目送著們的背影,耳邊不斷回著焦姣那句“顧家人無無義遲早會遭報應的”。又想起二嬸那神經質的笑容,“顧家只有你死我活沒有人倫道德,姓顧的里都流淌著罪孽,每個顧家人都罪有應得……”
是嗎?真的是這樣嗎?顧靈毓,為顧家當家人的你,是否也是這樣罪有應得?前方是不是也有報應在等著你?
如果這是真的,不管到底是怎樣,都希我們的孩子已經將一切罪孽都割干凈,就讓他替你贖罪,帶走一切你的報應和罪孽吧。
回到娘家后不久,傅蘭君拾起了學的教務,重新過起了家和學校之間兩點一線的生活。
流言蜚語在哪里都不能免,關于顧靈毓、傅蘭君和南嘉木之間那些桃新聞在學校里亦有生發芽的沃土,更何況學校的學生多是軍人家眷。阿蓓陪傅蘭君在學校里散步,聽到學生們竊竊談這件事,有人說如果不是傅校長給顧靈毓戴了綠帽子興許南嘉木不會死得這樣快,有人反駁說黨犯的是謀逆大罪怎麼可能姑息……阿蓓看傅蘭君的臉,傅蘭君神一如往常,這樣的話已經聽得太多,聽到麻木了。
猜你喜歡
-
完結111 章

誘甜
巴黎東方藝術作品展在Beatrix院館開展一周。期間,相關話題持續占領著法國推特tag榜。這是上流社會的年度慈善沙龍,以中世紀古堡風,沉浸式展現了一場東方視覺盛宴,參展作品無一不來自東方頂尖的藝術家。但今年,竟破天荒展出一副新秀畫作。據說是…
41萬字8 11839 -
完結102 章

我只喜歡你的臉
人都說末洺走大運了,本是個沒錢沒后臺的小可憐,就因為那張臉恰巧有那麼點像大佬韓劭烐的已婚白月光,就被韓劭烐帶回去寵上了天。聽說末洺死心塌地的跟了韓總三年,聽說末洺深愛韓總,為取代韓總的白月光用盡一切手段,后來聽說....韓總非要拉著人去領證…
32.7萬字8 11777 -
連載2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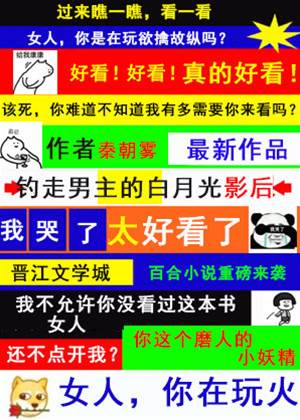
釣走男主的白月光影后
十八線小糊咖沈曼語出了車禍,穿成一本娛樂圈文里的惡毒女配。女配囂張跋扈,愛慕男主,處處與男主的白月光女主作對。沈曼語本不想摻合進這堆破事中。然而酒后走錯房間,她宿醉醒來,揉著酸痛的腰,映入眼簾的卻是女主微抬下巴,居高臨下的冷淡注視。…
5.7萬字8 513 -
完結163 章

顧少的小嬌妻
懸崖上。 層層歇斯底里的回聲充斥著耳邊,喻九墨將手中的天花斷書撕成碎片,狠狠的向懸崖扔去。痛徹心扉的、歇斯底里的。 天花……該死的天花!
45.4萬字8 647 -
連載264 章

名門盛嫁:四爺太豪橫!
世人都說病嬌四爺好。蘇顏:好什麼好?顧四爺:“專一,細腰,易推倒。” 傳聞星河集團總裁顧四爺高冷禁欲,獨斷專行,不近女色;可婚后呢,他夜夜溫香軟玉在懷,叫魂兒似的:“顏兒,顏兒,給爺唱個征服~”蘇顏,“誰,唱什麼?”四爺:“爺想給顏兒唱征服……”蘇顏:“嗯,唱吧我聽著呢。”婚后半年,誰他媽說我男人只有顏?分明還有八塊腹肌,18cmmmmm……男人:“噓……顏兒自己知道就好。” 【這是一個霸道千金,柔軟內心VS假病嬌/真腹黑的甜寵文】
48.4萬字8 870 -
完結231 章

掉馬后,被傅九爺圈在懷里放肆寵
男女主感情線無狗血無誤會,是甜文!! 星球大佬穿成謝家被找回的真千金,卻被人人嘲諷是個鄉下丫頭。 然而鄉下丫頭命好,有傅九爺護着。 衆人紛紛唾棄:呸!花瓶! 後來,國際著名占卜師、醫學聖手、武術大師,國際黑客…:求求大佬收我爲徒! 某神祕家族:恭請大小姐回家繼承家業。 傅沉夜:自我介紹一下,我是你們的姑爺。 得知真相的謝氏夫婦腸子都悔青了:“寶貝,爸媽錯了,你快回來。” 謝晚星勾脣一笑:“寶貝?除了傅沉夜誰都不能叫我寶貝。” 甜寵+強強+蘇爽+1v1雙潔+虐渣
35.6萬字8 31574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