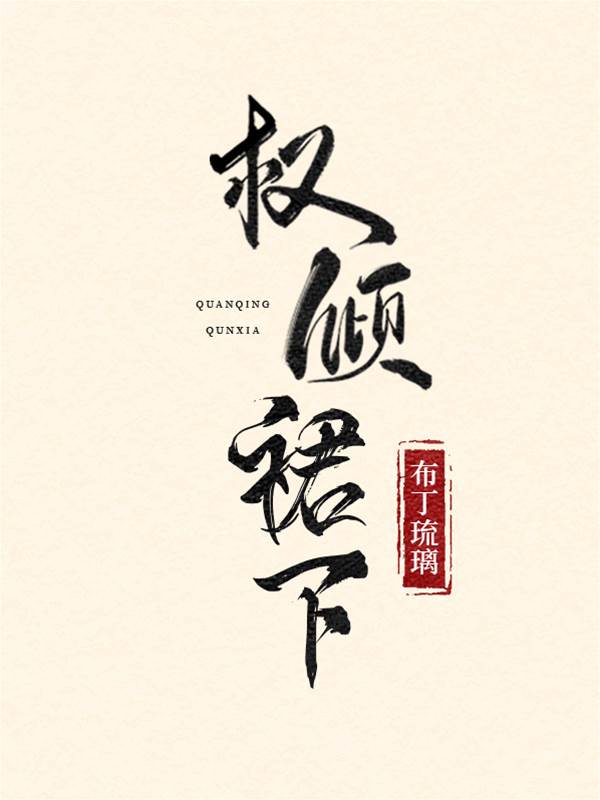《春為聘》 第 71 章 番外3
婚隊又行了數日, 在沿途的一座客棧落了腳。
深知未婚妻是個饞兒的,承牧分配好客房后,便吩咐店小二迅速備膳,所點的菜品也多是兒家吃的甜口。
得知承牧在點菜, 裴悅芙沒像其他待嫁子那樣矜持, 而是提著繁縟的長走到承牧邊,墊腳想要私語一句, 奈何個頭有些低, 挨不著男子的耳。
承牧適時地斜傾, 歪頭聽起的意見。
“我想吃生煎包。”吃過一次樂熹伯府的生煎, 裴悅芙意猶未盡, 提起時還了,差點到承牧的耳垂。
承牧側眸,看向小饞貓一樣的未婚妻,冰冷的面容沒什麼緒,但對提的要求幾乎有求必應。
可不是每家飯莊或客棧都會做生煎,這可為難到了店小二, “小店沒做過生煎包啊, 蒸包子可好”
裴悅芙顯然對蒸包子沒什麼興趣,卻又不想較真, 為難店家, 剛要點頭說“好”,就聽側的男子問向店小二“能借灶臺一用嗎”
聞言,店小二和裴悅芙同時看向了承牧。
承牧將袖管里的糖果全部倒給裴悅芙, 隨后擼起袖子走向灶房,凈手后就開始拌餡和面,拔魁梧的軀在仄的小屋里, 顯得格格不,神卻格外認真。
隨行婚隊的不侍從紛紛來圍觀,慨承將軍對未婚妻的用心和寵溺。
裴悅芙站在人墻外,聽著“噠噠”的切墩聲,角起弧度,捧著糖果回到客房,倒頭睡在了小榻上。
當生煎的特殊香氣飄散鼻時,裴悅芙很自覺地爬起來,眼看著承牧端著托盤走進來,袖管還挽在手肘的位置。
“你還會做面食呀”
裴悅芙盯著被擺放在圓桌的生煎,就差咽口水了。雖不知承牧的手藝如何,但觀外表,絕對是像模像樣的,薄薄的皮上還撒了一層白芝麻。
Advertisement
“很小就混跡街頭,什麼都要會一些。”
對于往事,承牧說得云淡風輕,可裴悅芙腦補出了他悲慘的年經歷,嗓子忽然發疼,快步走上前,勾住承牧的尾指,使勁兒晃了晃,“以后我都會陪著你,拉鉤。”
看頗義氣的樣子,承牧提提角,“快嘗嘗味道如何吧。”
“好。”
子嗓音哽咽,似乎真的與曾經的那個流浪街頭的年共了。
嘗了一口冒熱氣的多生煎,裴悅芙立即豎起大拇指,“不錯,你也嘗嘗。”
可桌上只有一副碗筷,以至裴悅芙在提議后,不得不厚著臉皮用自己的筷子夾起一個生煎遞送到了男子邊。
忐忑地等待著承牧下口,可男子只是靜靜看著,沒有開口的意思。
兩人量差距甚大,裴悅芙執筷的手有些發酸,卻不想被拒絕丟了面子,于是眼一橫,略帶質疑道“你不會是下毒了吧,所以不敢吃”
假兇假兇的模樣連小孩子都糊弄不了,可謂拙劣,然而承牧卻順了的意思,張開咬了一口,還被餡里的湯燙到了舌頭。
向來喜怒不形于的人,將這份炙燙連同那口生煎一并咽了下去,沒有表現出異常,“嗯,沒有失手。”
“真的很不錯”
找回了面子,裴悅芙笑著彎曲手肘,卻意識到,他只吃了一口,那剩下的一大半改由誰來解決掉
頓了再頓,又舉起手,喂了過去。
承牧沒有為難,在沒有吹涼的況下,吃下了一整個生煎,最后不得不為自己倒杯涼水下生煎的余溫。
自顧自吃起來的裴悅芙發覺了自己的心,雙腮一鼓,有點不知所措。
承牧飲了幾口涼水后,抬手拍了拍的后腦勺,“沒事,你先用吧,我去看看車隊的馬匹。”
Advertisement
目送男子離開后,裴悅芙用左手使勁兒拍了一下右手,較為自責。自己食用生煎時常會吹一吹里面的熱氣,怎會忘記提醒承牧呢
不過,承牧也是個木頭,都不覺得燙嗎
瞄了一眼半啟門外的廊道,裴悅芙吃下剩余的生煎,起推門走了出去。
待承牧回到客棧,剛與同伴們叮囑完明日一早啟程的時辰,就被裴悅芙拉進了的客房。
桌上擺放著一碗綠豆涼飲,應是小娘子特意為他準備的。承牧搖搖頭,“都過勁兒了,沒事的。”
“你喝嘛。”
裴悅芙獻寶般的捧起瓷碗,一副期待的模樣。
雖經歷了家族和牢獄之災,可裴悅芙在長兄和樂熹伯夫婦的關照下,沒經歷過多世態炎涼,也未因世態炎涼被磨平過棱角,故而,或許會在被拒絕后到失落和悵然。
而承牧同樣不愿產生失落的緒,更不會拒絕的好意,對上這麼一雙水靈靈的眸子,他接過碗,幾口喝下,眉沒皺一下,嗝也沒打一個,總是一副溫淡平靜的模樣,像是不會有任何緒似的。
若非在來往的書信中已建立了對他的了解,裴悅芙非要以為他對這門親事不甚上心,但實際上,裴悅芙比任何外人都知,他對這門親事的重視程度。那些含蓄晦的意,已通過文字傳遞到了裴悅芙的心里。
夜里,裴悅芙沐浴歇下,剛掖好被子就聽見幾聲詭異的鳴。
哆嗦一下,趿拉上繡鞋跑到墻角,隔著一堵墻叩了幾下。
客棧的隔音不是很好,一墻之阻的隔壁能清晰聽見叩叩的聲響。
承牧坐起,任被子落在腰,快步走到墻前,輕聲問道“害怕了”
聽力靈敏的他怎會沒察覺到窗外的鳴。
裴悅芙手做喇叭狀,合在墻面上,“承牧,你陪陪我說說話兒。”
Advertisement
“要我過去嗎”
“不用,就這麼說。”
承牧不自覺地笑了笑背靠墻面,目視被月籠罩的小窗,認真地“嗯”了一聲,“聊什麼”
裴悅芙也默契地靠在墻面上,歪頭問道“聊聊你的過去吧。”
在來往的書信里,他從未提及過曾經的自己,這讓裴悅芙產生了濃濃的好奇。
對于過往,或悲或喜,每個人的都是不同的,而承牧從不主與人提起自己灰暗的過往,但即便未婚妻問,他也沒什麼可瞞的。
承牧出生在皇城以北的一座小城的獵戶家中,奈何父母相繼離世,留下九歲的他獨自過活,后被城中武館的館主相中,收為關門弟子。
怎料,館主收他為弟子,并非惜才,而是為了他所剩無幾的家當。
被趕出師門后,他用從館主那里學來的武藝,打得館主頭破流,之后賣掉奪回的家當,只去往皇城謀生,卻因年紀小時常騙,還遭遇過人販牙婆,好在武藝傍,還順手從牙婆手里解救了幾個年紀相差不多的孩子。
那些年里,他做過不計其數的長、短工,也因子耿直,得罪過不雇主,挨過罵、吃過虧,就這樣一步步艱難地行進著,卻依舊不改初心,想要做一個懷有善心的人,不為紈绔子弟賣命,也不為無良商家做事,因著一子倔勁兒和一的好功夫。在偶然的機會,他得到了廣招能人異士的裴勁廣賞識,進而結識了裴衍。
正因為裴衍,他打開了心門,抬頭瞧見了燁燁璀。
思及此,他輕輕喟嘆,話音一轉,道“你可記得咱們初見的場景”
裴悅芙還在疼惜他的過往,聞言沒有反應過來,發著鼻音“啊”了一聲,帶著疑,隨即反應過來,重重點頭,“我記得。”
Advertisement
那日是十歲的生辰,正當被家人和仆人們簇擁著祝福時,忽見長兄帶著一個衫破舊的年走進來。
年高高瘦瘦的,帶了點滄桑,眉眼卻致如畫,與長兄的俊不同,有著罕見的頹然。
那日,喜歡熱鬧的不顧母親的叮囑,湊了過去,出白凈的小手,遞給年一塊新出爐的點心,還略帶傲地道“這是后廚專門為我做的。”
年沒接,第一次拂了的好意,也第一次知道,瓷娃娃一樣的小娘子是會記仇的,在之后的每一次相遇,都是扭頭就跑,絕不跟他多費一句口舌。
這麼多年過去,小娘子的傲未變,承牧也不會讓其因為世態炎涼而改變。
“你那時是討厭我嗎”
裴悅芙搖頭,著袖口推開門,徑自來到隔壁的房門前,叩響了門扉。
門扉被拉開的一瞬,裴芙悅鄭重地解釋道“我沒討厭過你,我是懼怕你。”
在裴衍邊歷練多年的承牧,在褪去青后,有著萬夫不可擋的驍勇,不僅令比武的對手而生畏,也令一向蠻的裴悅芙到陌生和膽。
話落,并未使承牧覺得輕松,反而泛起苦,“那,如今呢”
裴悅芙使勁兒推開擋在門口的他,氣勢洶洶地了進去,反腳帶上門,叉腰道“我若還懼怕你,會同你互許心意”
這算當面表白嗎承牧下意識向后退了半步,“是從”
那次救,才有所改觀的吧。
可承牧不想提及那段對而言可怕的經歷,便轉移話題,道“你離得太近了。”
裴悅芙還雄赳赳地叉著腰,在被提醒后,方覺赧,但夜深人靜最易放大人的愫,咽咽嗓子,既主又怯怯地問道“承牧,你能抱抱我嗎”
自從被救起,就迫切地被他抱進懷里,有著濃濃的踏實。
聽過的話,承牧定眸凝視著矮了自己許多的子,在黯淡的線中慢慢抬起手,環住了子的肩,輕輕帶進懷里。
這個擁抱,如紙張純白,沒有旖旎,不染念。
裴悅芙發現,承牧不僅是大冰塊,還不解風,可就是這樣無關風月的擁抱,才會讓更為自在,也更容易接納和信任這個男子。
“承牧。”
“嗯”
男子的聲音在不自覺中變得溫悅耳,令裴悅芙覺得耳朵的。
在承牧的膛上蹭了蹭耳朵,裴悅芙悶聲道“你可以再抱一些。”
冷峻的男子紅了面龐。
子的段韌,比抱著被子還要舒服,承牧試著一點點收手臂,將子勒在懷中,卻不敢太用力,擔心沒掌握好分寸勒傷子,畢竟自己的力氣一向很大,徒手可掰斷刀劍。
倏然,一聲鳴響徹在郊野之上,清晰耳,裴悅芙嚇得一激靈,摟住承牧的腰。
承牧哪哪都,環在他的腰上,像是環住了堅的鋼,硌到了雙臂,可裴悅芙還是倔強地不愿松開,化作夜里的鳥兒,棲息在了“鋼質枝頭”上。
從未懼怕過什麼的男子還是細膩地捕捉到了子的恐懼,猶豫著抬起右手,落在了的發頂,小心翼翼地抓起來。
順的發穿在指間,仿若在綢上。
“小芙,別怕。”
生疏的安吐出齒時,承牧任命地閉上眼,這輩子算是栽在手里了。
裴悅芙悶悶地應了一聲,抬手抓住了他在發頂的大手,強行地十指相扣,自害怕野的,用自己的方式紓解著恐懼。
細膩的在月和燈火的織映照下,呈現出雪白幾近亮的澤,與男子古銅的差別甚大,宛如夜里的一抹皎白月,傾灑環繞在了古松旁。
承牧低頭看著明顯的皮差,不知想到了什麼,俊面更為燒燙,可他始終規規矩矩的,守禮又溫。
這晚,兩人相擁到后半夜,直到裴悅芙再也頂不住歪頭睡去,承牧才松開彼此握的手,打橫將之抱起,走去了隔壁房間。
倚在客房外守夜的店小二沒有瞧見承牧從子的房中走出來,暗自嘖嘖兩聲,心道最容易引燃了。
可令店小二沒想到的是,承牧此刻正獨自躺在自己的客房中準備睡。
適才將裴悅芙送回房后,為了給房門上栓,他棄門選窗,憑借矯健的手回到了自己的客房,都未一下,氣息平穩地不像個尋常人。
次日一早,當承牧從房中走出去時,捕捉到了店小二詫異的目。
“怎麼”
“沒、沒事,爺要晨練嗎”店小二撓頭傻樂,很是不解承牧是何時回的房間。
猜你喜歡
-
完結2328 章

傲世帝妃:爺你太囂張
“本尊就是修羅,殺人,自然不眨眼。” 一朝重生,她尋丹解毒,重新修煉。廢物?呵,她神器在手,靈獸全收!廢物?你見過廢物殺人不眨眼,見過廢物攪動風雲變幻麼?她雲暮挽要走的路,沒有人能夠阻攔,然而,修煉之路漫漫,總有小妖精想要勾走她。於是乎,就出現了這麼一幕 “滾,該死的男人。”她氣急。 “遵命,夫人。”某人坏笑。
256.2萬字8.09 1209107 -
完結13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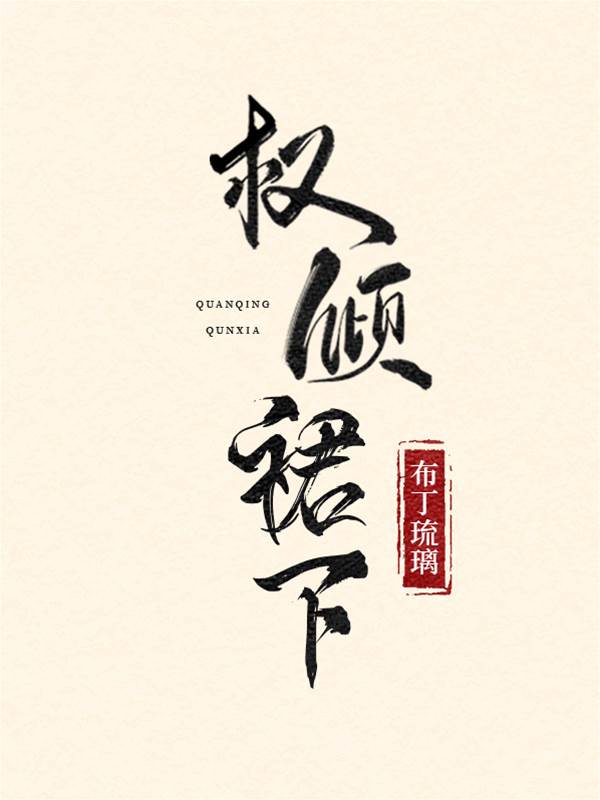
權傾裙下
太子死了,大玄朝絕了後。叛軍兵臨城下。為了穩住局勢,查清孿生兄長的死因,長風公主趙嫣不得不換上男裝,扮起了迎風咯血的東宮太子。入東宮的那夜,皇后萬般叮囑:“肅王身為本朝唯一一位異姓王,把控朝野多年、擁兵自重,其狼子野心,不可不防!”聽得趙嫣將馬甲捂了又捂,日日如履薄冰。直到某日,趙嫣遭人暗算。醒來後一片荒唐,而那位權傾天下的肅王殿下,正披髮散衣在側,俊美微挑的眼睛慵懶而又危險。完了!趙嫣腦子一片空白,轉身就跑。下一刻,衣帶被勾住。肅王嗤了聲,嗓音染上不悅:“這就跑,不好吧?”“小太子”墨髮披散,白著臉磕巴道:“我……我去閱奏摺。”“好啊。”男人不急不緩地勾著她的髮絲,低啞道,“殿下閱奏摺,臣閱殿下。” 世人皆道天生反骨、桀驁不馴的肅王殿下轉了性,不搞事不造反,卻迷上了輔佐太子。日日留宿東宮不說,還與太子同榻抵足而眠。誰料一朝事發,東宮太子竟然是女兒身,女扮男裝為禍朝綱。滿朝嘩然,眾人皆猜想肅王會抓住這個機會,推翻帝權取而代之。卻不料朝堂問審,一身玄黑大氅的肅王當著文武百官的面俯身垂首,伸臂搭住少女纖細的指尖。“別怕,朝前走。”他嗓音肅殺而又可靠,淡淡道,“人若妄議,臣便殺了那人;天若阻攔,臣便反了這天。”
52.5萬字8 22091 -
完結318 章

侯府長媳
謝景翕的二姐難產而死,留下一對孩子,謝景翕就在這種情況下嫁進安奉候府,做了二姐夫的填房,在經曆雙子夭折,娘家放棄,夫君的不信任後,謝景翕選擇獨居別院十幾年,卻不料最終還是被人害死。 重生後的謝景翕決定這一世一定要為自己而活,找出殺害自己的兇手,然而孤立無援的她,注定要因此走上一條充滿血腥的道路。 隻是走著走著,謝景翕突然發現,她身後那個出了名的病秧子夫君,竟是比她還要心狠手辣……
88.4萬字8 26667 -
完結1427 章

娘娘是個嬌氣包,得寵著!
現代牛逼轟轟的神棍大佬林蘇蘇,一覺醒來發現自己成了個棄妃,還是有心疾那種,嬌氣得風吹就倒。爭寵?不存在的,鹹魚保命才是生存之道!可偏偏,身邊助攻不斷!太后:趁著皇帝神志不清,快快侍寢,懷上龍子,你就是皇后!林父:皇上受傷,機會難得,閨女快上,侍疾有功,你就是皇后!只有宮妃們生怕她林蘇蘇一朝得寵。於是!今日宴席,皇上微熏,絕不能讓林蘇蘇去送醒酒湯!遂,一眾妃嬪齊心協力,把林蘇蘇困在了冷宮。可誰來告訴她! 冷宮那個眼尾泛紅的男人是誰啊!到底是哪個不長眼的,又把皇帝送到了她眼前啊!!
128.6萬字8 75471 -
連載917 章

神醫毒妃天才寶寶
21世紀天才女軍醫鳳菁,遭人暗算,魂穿大燕朝,成為鎮南候府肥胖花癡,未婚先孕的嫡長女,還被誘哄著代替妹妹嫁給了手握重兵,權傾天下的晉王。 鳳菁想死的心都有了,可看了看身邊瘦如小雞崽的小家伙們,終是無法狠心。 結果小雞崽們比她還要想死,先是服毒尋死,然后絕食尋死,最后來個跳河自殺。 鳳菁心累:“算了,要死大家一起死吧。” 小家伙們卻紅了眼眶:“娘,你別死,我們乖乖聽話。” 晉王火大的看著一家人:“再敢作妖,本王處死你們!” 后來,她的夫君成了大燕高高在上的皇帝,金口玉言賜封她為皇后。 她的一個兒子成了尊貴的太子,一個兒子成了賢名遠播的賢王,一個兒子成了大將軍王,一個兒子成了富可敵國的富貴王。 她是天下最尊貴的女人!
173萬字8 64786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