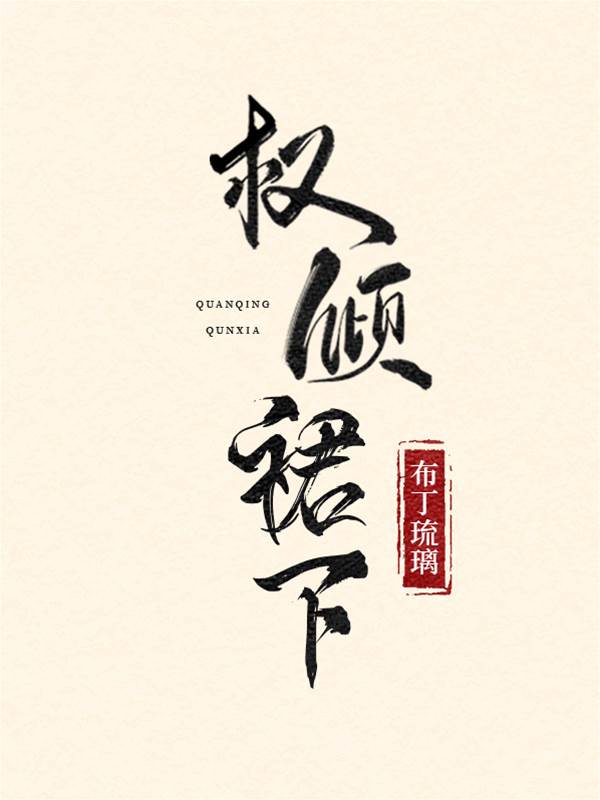《扶搖皇后》 璇璣之謎 第十七章 相思如此
誰知道後悔的滋味。
誰知道相思的滋味。
誰知道在相思裡後悔的滋味。
正如這長夜裡風慢慢的涼,冰般的穿過掌心,像往事無聲無息的從記憶的那頭踱來,戴青面,一雙深黑的沒有眼白的瞳孔,那麼冷冷的面盯上你,瞥一瞥,心便“咔嚓”一聲,裂了。
十餘年不過一夢。
WWW● ttκǎ n● c○
一夢裡一襟餘恨宮魂斷,年年翠庭樹。
一夢裡十年淒涼,似清湖燕去吳館巢荒。
一夢裡六朝舊事如流水,但寒煙衰草凝綠,一夢裡舊遊無不堪尋,無尋惟有年心。
原來一夢。
他慢慢的轉手中酒盞,在高樹之上,對著更高的月,遙遙一敬。
月清涼,如這杯中酒冷冽,清凌凌的在掌心中掠過,又像是那一刻的眼神。
就著那樣的眼神喝下這杯酒,便生生喝了苦酒,苦至此生未曾領略過的滋味。
十四年前,他亦品過那樣的滋味。
那一年他失了信,毀了諾,然而便失去了他的小小孩。
那一年他在黑暗的櫃子裡邂逅。
那一年他在牀褥下尋著那朵小小玉蓮花。
那一年他聽見說,是含蓮出生的最高貴的公主。
那一年他迎著的目,明明淚模糊卻還給了他一個令他震撼的屬於人滄桑而震撼的笑容。
那一年他將放在膝上,梳五年沒梳過糾結的發,很好的髮質無人打理,滿頭生,他慢慢的理那髮,心上也像長了葳蕤的草。
那一年他將抱在懷裡,裹在厚厚的披風裡,五歲的孩子長得像三歲,輕得像一歲,抱著像抱著一隻貓,極其安靜而乖巧。
Advertisement
那一年他原本打算帶走,然而他突然聽見師叔的聲音。
還隔著一個宮室的師叔傳音要他過去一下,見見玉衡,他便將放回,準備見了玉衡再回頭帶走。
走到一半看見八歲的孩匆匆而來,神欣喜而急切,他約聽說過這位公主對他很興趣,曾經專門遣使到無極拜訪,致上問候,他對那樣的問候敬謝不敏,而那個年紀的他,還是年,敬謝不敏便真的是敬謝不敏,不知道迂迴婉轉不知道曲意逢迎,三十六計,躲爲上。
他躲在宮牆之後,聽師叔和玉衡在說話。
師叔似乎有點不忿,語氣不太好聽。
“你看我那師兄,多事子永遠治不了,整日以天下正道爲己任,這世間那麼多魈魅魍魎怪道邪,豈是他們一門能消滅完的?這不,坐關坐得好好的,突然說天降妖,擾天地平衡,須除之,說我在遊歷江湖,正好,順手給解決了。”師叔手指一敲桌子,嘖嘖連聲,“笑話,茫茫人海,到哪找一個大活人?”
屋子裡玉衡也在笑:“你還有解決不了的事?這世上除了你師兄和你門中那羣長老,還有誰是你解決不了的?再說你師兄既然有這個吩咐,肯定有說是什麼人的。”
“嗤——”師叔鼻子裡哼了一聲:“就給了個大概的生辰,並說那子多半出生時帶有異象,可我在天下找了五年了,也未曾聽說過誰出生帶有異象,而生辰八字——孩兒養在閨中,到哪裡去問人家生辰八字?”
“什麼生辰八字?”玉衡似乎在不急不慢的喝茶,半天才問:“有機會我也幫你探聽下。”
師叔便說了。
他當時便一震。
Advertisement
那生辰八字,和的只差一天,而……含蓮出生。
是嗎是嗎?
是吧是吧。
的眼神那麼奇特,明明只是五歲孩,目裡卻滿是對這世事和人生近乎徹的了悟和悲涼,五歲的孩子,知道疼痛,卻未必懂得那般沉重的悲涼。
五歲的孩子,被關在櫃子裡,滿褥瘡面黃瘦骨節變形,最大的可能是殘疾弱智,然而說話清晰言辭明朗反應敏捷,甚至還有小小的幽默和古怪的言辭。
,不是普通的孩子。
他心沉了沉——原本他還想著,帶走,如果有機會的話向師傅求懇,也收門下,給一份安定強大無人敢於再欺負的明生活,然而現在看來,不能了。
他還要隨師叔回師門,帶著遲早會被師叔發現,他師門中人都有大神通,小小的絕對瞞不過師叔,更不可能瞞過靈機通神的師尊。
他猶豫一刻,轉想趁師叔還沒出來,趕先把送出宮,想辦法找人寄養,以後從師門回來再接走。
然而他剛轉過子,師叔已經飄了出來,招呼他,走了。
他無奈,只好隨師叔離開,一路上他強著自己不能回頭,卻總在恍惚中似乎聽見扶窗呼喚的聲音,聽見不知道在哪裡發出的求救和哭聲,他在那樣的幻境裡臉蒼白,飽折磨,師叔發覺了,還取笑他怕璇璣公主何至於怕這樣,他怕師叔發覺,只好忍著,勉強的笑。
當晚師叔又拉著他練功談武,這也是以前的慣例功課,那晚他心急如焚坐立不安,幾次試圖打斷師叔,連催眠都冒險使了,結果除了讓師叔產生疑外,別無作用。
Advertisement
沒有辦法,師叔太過強大,不是十三歲的他可以應付,即使是現在,他也不能。
直到第三天,他才找到一個可以離開師叔的機會,一路狂奔回頭去璇璣皇宮。
他來遲了。
人去屋空,那櫃子空空的開著,不僅那屋子,連整個宮室都空了。
更讓他心神發冷的是,滿屋子飄著濃厚不散的腥氣味,他甚至在已經洗過的地下青磚裡,發現已經發黑的跡,麻麻到都是,甚至還有細微的屑,而那張牀上,乍一看沒什麼特別,只覺得似乎變了,發白變發黑,散發著濃重的腥氣,用手一,滿手淡紅。
要多的鮮流出,才能把一張牀整個染?
他立在那裡,立在秋夜如水的月裡,那一霎,從頭到腳,冰冰涼。
誰遭遇了天下最慘的酷刑?誰發現了躲在櫃子裡的孩?誰死在這張牀上將遍橫飛,誰知道那五歲的小小孩子,在這三天裡面對了什麼?
他甚至找不到人去詢問——整個盈妃宮中的人,大多都死了,連盈妃據說都“暴斃”了,他也沒有太多時間去查證,他還得趕回師叔邊。
他來時一路狂奔,去時步履蹣跚,的生死不明,他的失信錯過,像是一道鐵索,牢牢鎖著他心頭,從此再無一日卸下過。
後來他試著向璇璣提親——他抱著萬一的希,假如是旋發現了呢?旋發現了便有活路,無論如何虎毒不食子,也許孃親會被殺,也許盈妃會被遷怒,但是作爲皇的,無論如何是皇族脈,璇璣皇后再跋扈,也無法當著旋的面殺掉他兒。
他求娶“璇璣陛下最小的,含蓮出生的兒。”
Advertisement
他不知道的名字,他也知道沒有名字,只能這樣形容。
那頭很快有了迴音,璇璣皇帝欣然應下,得到消息時他狂喜萬分,以爲確實被旋救下,但是雙方換庚帖時,他知道,有人冒名頂替了。
庚帖上是淨梵,生辰八字也不對,而此時五洲大陸也開始傳開淨梵含蓮出生的傳說,但是似乎沒有人想過,爲什麼到淨梵八歲,纔會傳出含蓮出生的說法?
而淨梵這個名字,如果他沒記錯的話,當初小公主遣使求見他的時候,拜帖上寫的是“淨繁頓首。”
一字之差,爲了向佛陀蓮花靠攏,連名字都改了。
而世人聽見那些傳聞,往往也不會多想,這樣一年年傳下來,淨梵便真的含蓮出生了,隨著年深日久,越發沒有人想得起當初那個含蓮出生的傳說發生的日期。
但他記得,但他知道。
他堅決要求退婚。
爲此他遠赴璇璣,旋爲了挽回婚姻,連璇璣圖都拿出來了,這圖一拿,他反而更確定淨梵見過那孩子。
如果沒見過,如何能知道璇璣圖的容?
既然見過,便是那慘案發生的最大嫌疑人,他爲此對施了攝心之,當年他那功力還不純,但是勉勉強強也出了那夜發生的事。
果然是淨梵告了,皇后暴怒,當即命人對許宛施刑,並理掉了無名。
淨梵的記憶到了許宛施刑那裡便模糊不清——小小年紀的看見那樣慘烈的一幕,縱然天賦涼薄也承不起,也直覺的避開了。
他卻被那“理”兩字打擊得一個踉蹌,扶住樹久久不能言語。
那一刻他注視著一臉茫然的淨梵,在這個小小孩臉上看見繼承自璇璣皇后的狠毒冷,這個孩子,殺了另一個孩子,小小年紀蛇蠍心腸,竟然還試圖欺騙他,有什麼理由留著?
他出手去——卻被玉衡攔下。
玉衡從來都是們母的保護神,也常年居在璇璣皇宮,多年未曾離開璇璣。
正因爲他在,還是年的他,沒有辦法殺掉他想殺的人,沒有辦法更進一步在璇璣皇宮查探那夜真相,那個強大的、偏偏又對那蛇蠍子忠心耿耿的男人,是橫在們面前的一道無可撼的保護的牆,無論旋,還是他,那時都越不過。
他默然離開,武力不敵還有別的辦法,最起碼他可以不要那個假蓮花。
他用盡手段終於退了婚,至於璇璣皇室那個而不宣的要求,他無所謂,總之無論如何,淨梵永遠不會是他的妻子。
但是那個小小孩兒,他卻直覺的認爲,沒死。
他不相信會死,那個奇特的、眼眸明亮而蒼涼、歷經五年最黑暗歲月依舊不改本裡芒閃爍的子,上天讓其降生必然有其使命,不該無聲無息被命運解決,換得早夭的下場。
他要找到,然後讓自己決定要不要報仇,他要將那些人留給去親手報仇,如果這輩子找不到無名,他會趕在們死之前,幫解決。
後來他懶於政治,有點時間便微服出遊,希有機會見記憶裡眼神滄桑的孩子。
然後那年那一夜,太淵玄元山上天地森涼,月下松濤陣陣,他在月中舞劍,驀然回首看見被人推下山崖的子,從山崖下緩緩升起。
他看見的眼眸,明銳、森涼,帶著不屬於那個年紀的淬火般的滄桑。
那樣的滄桑,如此細微又如此深重,在那年輕的臉上如此不協調——就像很多年前的那個五歲孩子,用五歲的容,傳遞二十多歲般的悲涼。
他的心在那一刻微痛,爲這般深藏在記憶裡瞬間重疊的眼神。
於是他破例,接近——自從淨梵之後,他其實很不願意靠近人。
接近,知道,知道,重疊,重疊,上。
那些日子裡,從遙遠的五歲奔來,和他的記憶漸漸一一縷的對上,有了太多的改變,相貌神,甚至連骨骼都胎換骨,然而那眼眸中神采不變,那黑暗歲月裡勇於堅持的氣質不變,那逆境中時時保持心強大的堅毅不變,那遇見溫存和戲謔後不自然的尷尬和失措,不變。
然而從此他便懂得了什麼患得患失。
失去了五歲之前的記憶,他對此又喜又憂,喜的是那樣悲哀的過去,不記得也好,忘記那些苦,忘記他的失信毀諾的錯,還能保留住一個心完整潤、不曾被世事狠辣之刀狠狠傷害的;憂的是任何記憶封鎖,其實都有期限,而一旦有朝一日記起,卻又要如何面對?而一旦記起,他又如何面對?
猜你喜歡
-
完結23 章

法醫狂妃:王爺,躺好彆動!
首席女法醫冷夕月,穿越成寧王李成蹊的棄妃。 剛剛醒過來,就遇到冤案。 她帶著嫌疑人家屬偷偷去驗屍,卻被王爺拎小雞一樣捉回去狠狠訓斥。 她費儘心思追查死因,最後嫌疑人卻跪地求她不要再追查下去…… 找出真相,說出真相,她執意要做逆行者。 可糊塗王爺整日攔著她就算了,還弄來個“複生”的初戀情人來氣她…
4.4萬字8 7755 -
完結13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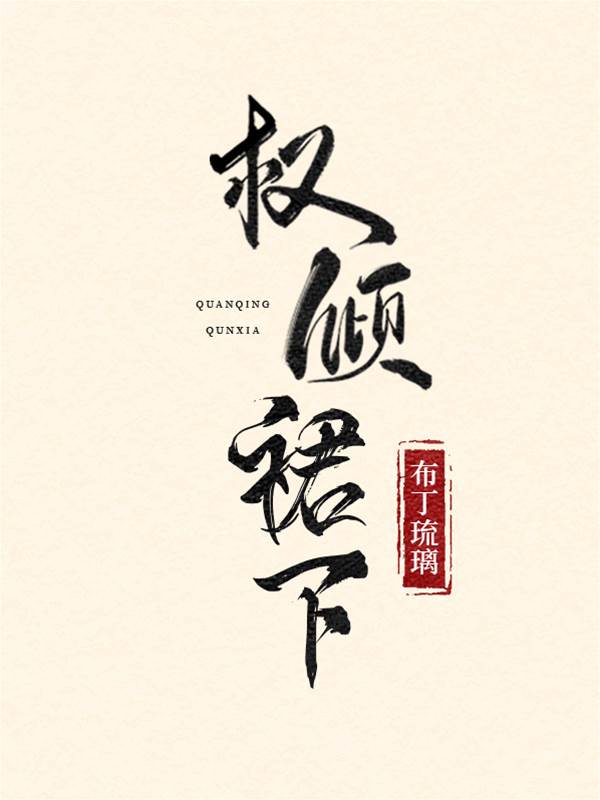
權傾裙下
太子死了,大玄朝絕了後。叛軍兵臨城下。為了穩住局勢,查清孿生兄長的死因,長風公主趙嫣不得不換上男裝,扮起了迎風咯血的東宮太子。入東宮的那夜,皇后萬般叮囑:“肅王身為本朝唯一一位異姓王,把控朝野多年、擁兵自重,其狼子野心,不可不防!”聽得趙嫣將馬甲捂了又捂,日日如履薄冰。直到某日,趙嫣遭人暗算。醒來後一片荒唐,而那位權傾天下的肅王殿下,正披髮散衣在側,俊美微挑的眼睛慵懶而又危險。完了!趙嫣腦子一片空白,轉身就跑。下一刻,衣帶被勾住。肅王嗤了聲,嗓音染上不悅:“這就跑,不好吧?”“小太子”墨髮披散,白著臉磕巴道:“我……我去閱奏摺。”“好啊。”男人不急不緩地勾著她的髮絲,低啞道,“殿下閱奏摺,臣閱殿下。” 世人皆道天生反骨、桀驁不馴的肅王殿下轉了性,不搞事不造反,卻迷上了輔佐太子。日日留宿東宮不說,還與太子同榻抵足而眠。誰料一朝事發,東宮太子竟然是女兒身,女扮男裝為禍朝綱。滿朝嘩然,眾人皆猜想肅王會抓住這個機會,推翻帝權取而代之。卻不料朝堂問審,一身玄黑大氅的肅王當著文武百官的面俯身垂首,伸臂搭住少女纖細的指尖。“別怕,朝前走。”他嗓音肅殺而又可靠,淡淡道,“人若妄議,臣便殺了那人;天若阻攔,臣便反了這天。”
52.5萬字8 22143 -
完結429 章
乞丐醫妃:馭夫有道
穿越成乞丐,救了個王爺?這是什麼操作?江佑希不由暗自腹誹,別人都是穿越成公主王妃,她倒好,鞋兒破帽兒破身上的衣服破? 神仙運氣呀。 還被這個惡婆娘冤枉和敵國有勾結,勾結個毛線,她連去敵國往哪個方向都不知道啊! 火速止住謠言,她毫不留情地報復......了惡婆娘,在王府混的風生水起。 她真是馭夫有道啊! 馭夫有道!
108萬字8 10213 -
完結454 章
山河美人謀
有仇必報小驕女vs羸弱心機九皇子未婚夫又渣又壞,還打算殺人滅口。葉嬌準備先下手為強,順便找個背鍋俠。本以為這個背鍋俠是個透明病弱的‘活死人’,沒想到傳言害人,他明明是一個表里不一、心機深沉的九皇子。在葉嬌借九皇子之名懲治渣男后。李·真九皇子·策“請小姐給個封口費吧。”葉嬌心虛“你要多少?”李策“一百兩。”葉嬌震驚,你怎麼不去搶!!!
108.6萬字8 10188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