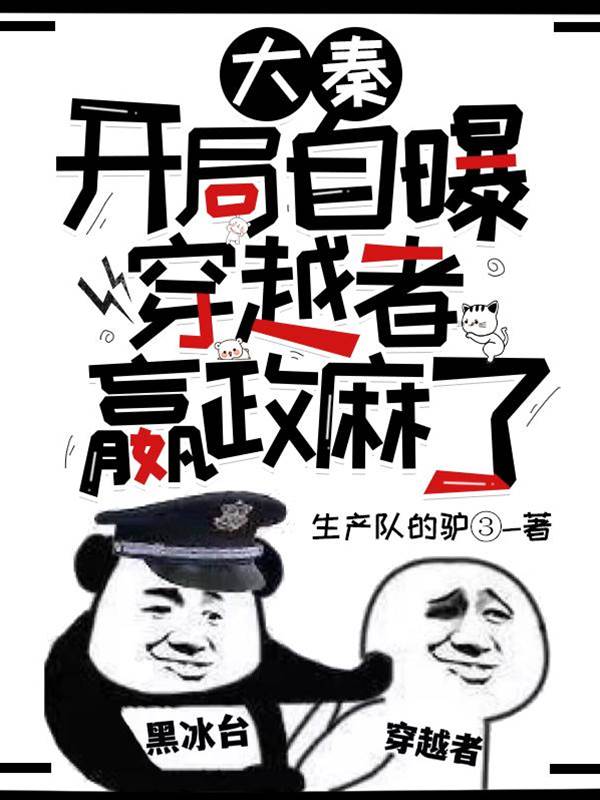《乾隆皇帝——雲暗鳳闕》第九回 赴喪府和珅聞儷歌 召金殿錢灃蒙知遇
他前面的話說得細緻微,眾人都是側耳聆聽,末了結論卻否定了乾隆和阿桂既定「八月進軍」的決策,又聽得大家心頭一震,都不悚然容。
「你方才說開支浩大,」紀昀是個癮君子,特旨允許前會議上吸煙的,但今天屋小人多,他不敢,手裡把握著大烏木煙斗會意而已,一邊聽著,沉道:「日期再推兩季,豈不是更加役大投艱?」
「大軍收回營,只用常例供應,氂牛、帳篷、車馬、輜重、被服——一大筆運輸消耗也就省下了。」李侍堯似乎有點,乾咽一口看一眼乾隆的茶杯,又移到了別。阿桂笑道:「我還是主張秋季進軍,秋季草高馬,利於騎兵長途奔襲。」李侍堯含笑說道:「我想敵人集中在南疆,若論草高馬這一條,無論如何我們也比不上霍集占。」于敏中道:「春季進軍冰雪融化,道路翻漿,不利於行軍,這是我聽隨赫德說的——你這個建議奇!」
李侍堯瞟一眼這個新貴,看見於敏中這副故作雍容的模樣他就生厭。但這是在乾隆面前,又是頭一次議計軍國大事的前會議,無論心裡怎樣想,人人都是溫文爾雅重沉穩姿態,他吭了一聲,說道:「你說得對,春季出兵,敵人萬萬料不到,正應了一個『奇』字,隨赫德在天山,有些道路確實春季翻漿,但青海向西一路沙漠翰海,最缺的就是水。沒有翻漿的事,我倒擔心士兵用水供應不上吶!」
兆惠和海蘭察對視一眼,都又避開了去。兆惠是從前方趕回來的,海蘭察也曾去過烏魯木齊,他們都是帶久了兵的老行伍。李侍堯這些話可說是都是一矢中的之言,但乾隆方才說過:將軍怕打仗、文都錢,如今的事還了得?平息阿睦爾撒訥叛,兆惠沒有用本部人馬,帶了額敏和玉素布兩部五千人直搗敵,不旬日間就平了準葛爾,將軍意氣何其雄也!若不是雅爾哈善玩敵誤國,庫車城早已拿下來了。海蘭察也在乾隆跟前立了軍令狀,「滅此朝食時不我待!」又訓斥六部:「畏難怯戰,一味招,連天朝大都不顧!」……急於取勝心切溢於言表……他們自己覺得已經被乾隆的話「」到了退無可退的角落。儘管李侍堯的話都對,不敢也不願附和,那樣,乾隆就太失了。
Advertisement
「春季進軍,李侍堯想得是。」乾隆突兀說道,眾人都發怔間,乾隆咬牙獰笑道,「但不是後年春。會議之後,阿桂、兆惠、海蘭察要即刻離京,明年開春由兆惠前敵,速平和卓之。」
現在已是十一月——明年開春進軍!即便此刻立即散會,還要和六部急磋商籌備,調度各路糧秣供應,商計進軍計劃,還有六千里冰天雪地遙途才能趕到哈大營——所有的人都被他這突然冒出的決策震驚了,一時竟人人僵坐如偶!乾隆剎那間心中閃過一猶豫,但帝皇至高無上的威權和自尊阻止了他改口,他很快就平靜下來,暗自噓了一口氣,格格一笑,問兆惠、梅蘭察:「二位將軍,你們看如何?有什麼難,只管說!」
「皇上睿聖天縱,英斷明決,奴才遵旨!」兆惠知此刻無論如何不能掃了乾隆的興,一邊心裡急速轉著念頭算計「難」,應聲答道:「霍集占兄弟忘恩負義人心喪盡,回部叛眾窮蹙一隅勢單力薄。再者,他萬萬想不到我軍明春進軍,以有道滅無道,以有備攻無備,可勝算!」說著,心裡已有了章程,一俯又道:「皇上,這樣打,不能全軍齊推,只可大軍遙相呼應近和卓。奴才願帶五千人直和卓,請萬歲下旨六部,一是馬匹、二是糧食、三是草料,三月之前必須運到烏魯木齊。運不到,也請以軍法從事!奴才請旨,由海蘭察掠軍策應,這樣,我們老搭檔合力作戰,我在前頭打得放心。」海蘭察心思靈還在兆惠之上,介面就道:「萬歲爺養活我們廝殺漢作麼?你只管在前頭掃,把我營里馬銃鳥銃葯槍都給你,咱們給主子作臉看,就是馬革里,我這頭出不了疏!」
Advertisement
本來一派張嚴肅的氣氛,海蘭察一句「馬革里」頓時逗得眾人一樂,阿桂此時也已想明白,乾隆要急戰,臣子萬萬要比他還急才能愜懷聖意,算了算也有一多半勝機,湊著一勞永逸了也罷,這樣想,心頭略寬了些,笑道:「這麼著,明日我親自主持兵部戶部會議,主事以上堂一律出席,由你們二人按需項提出來,是哪個司的差使就當堂布置了。然後我三人就辭駕出京。差使辦不好,咱們三個都『馬革里』回來見主子!」紀昀笑道:「軍機會議上都鬧出『馬革里』了,海蘭察讀的好書!」和珅笑道:「那馬革裹——海蘭察認真看清了麼?——他在下頭也是八面威風,就說錯了也沒人敢正他的誤。」海蘭察紅著臉一頭笑道:「主子,怪不得上回在兵部說馬革里他們都笑,高梧還說『都不告訴他,他糊塗到死!』如今才恍然大悟過來!」
「這才是個振作的樣子!」乾隆大笑道,「兆惠前鋒,海蘭察殿後,直葉爾羌,給朕痛痛地剿!班師凱旋日子,朕十里郊迎得勝將軍!」
「喳!」海蘭察、兆惠起來昂然答道。海蘭察皮臉兒一笑又道:「奴才們準能揍得霍集占兄弟恍然大悟過來!」
眾人立時又哄堂大笑,乾隆笑著擺手,說道:「阿桂、侍堯和兩位將軍,你們跪安吧。阿桂傳旨給禮部、務府,兆惠、海蘭察的兒子授三等車騎校尉,補進乾清門三等侍衛!去吧!」
「喳!」
四個人齊伏叩地大聲答道,起哈腰卻步退出殿去。
炕下八個人去了四個,頓時空落了許多。乾隆坐得久了,想挪下來,又坐回了子,神變得凝重起來,獃獃地盯視著暖閣隔扁瓶架,良久,嘆息一聲道:「軍務上的事,由著將軍們去籌劃吧。了你們進來聽聽,也好知道朕為政之難。眼下一是賑災,發放冬糧,春耕種糧,二是春闈科考,不能再鬧出舞弊賣的拆爛污事兒——這都是大局。阿桂去了,自然是紀昀、于敏中同李侍堯辦理,務必不能荒怠了。朕在京,可以隨時進來請旨的。國泰的案子一直拖下去不好。他是諸侯一方的封疆大吏,也是國恩的滿洲簪纓子弟,朕一直等著他有個謝罪摺子,能不驚朝局緩辦了最好。看來,他還真的是天各一方皇帝遠,仍舊在那裡為所為!」說著抬起臉來問窗外卜義:「錢灃進來沒有?」
Advertisement
「回主子!」卜義在窗外應聲答道,「來了有半個時辰了,奉旨在王廉房裡等候召見!」
「進來吧。」乾隆吩咐一聲,端茶啜著,已見錢灃步履從容,橐橐有聲踩著臨清磚地進殿來,乾隆微笑著看他行禮,溫聲說道:「起來吧,挨著和珅坐——朕來紹介:這是紀昀、這是于敏中、這是劉墉、這是和珅……都是你聞名不曾謀面的……」
他一邊說,紀昀已在審視錢灃,只見他穿著獬豸補服,頭上戴著的藍寶石頂子端正放在杌前的茶幾上,靛青的薄棉洗得泛白,套在九蟒五爪袍子里。腳下靴里套的布,還有馬蹄袖裡的襯都是漿洗得乾乾淨淨老棉布,瓜子臉上一雙細眉又平又直,眉梢微微下垂,黑瞋瞋的瞳仁閃爍著,幾乎不見眼白,下頦略略翹起,綳著,似乎隨時都在凝神聆聽別人說話,紀昀不暗贊,怪不得乾隆垂,這份凝重端莊練達宇,一見就令人忘俗!何況這麼年輕的!于敏中也掂掇:此人年老。劉墉也覺此人大方從容。只和珅想,這要算個男子了,顴骨似乎高了點?鼻樑又低了點……錢灃沒有理會眾人注目自己,聽乾隆介紹著一一頷首欠一口昆明腔說道:「謝皇上!不敢當皇上親自紹介——學生錢灃久在奉天,多赴外任,疏於向各位大人聆聽請教,日後奔走左右,盼能時加訓誨!」
「朕還是要紹介清白。」乾隆微微笑著又道,「他與竇鼐是同年進士,十六歲翰林院為庶吉士,十九歲進教館檢討,二十歲選江南道監察史、改授奉天史。高恆一案他第一個明章彈劾,勒爾謹、王亶一案已經寫好奏章,劉統勛告知了朕,是朕特旨改為奏——朕是深恐他得罪權貴太多啊!所以特簡調奉天……這次國泰之案,他又是首發。」他頓了一下,又道:「他與竇鼐有所不同,竇鼐指摘佞,只是勇猛無前,不計利弊,此人發微見著毫不容,但卻執於中庸、衡以大道,這就比竇鼐更為難能了。」
Advertisement
他很這樣長篇大論評價人,更遑論錢灃還只能算個部院小吏,幾個大臣都聽得不自在,目視錢灃時,雖然也有點局促,卻不顯得慌無措,雙手膝端坐,紅著臉道:「這是皇上勉勵!臣草茅後進識陋見淺,出於蓬蒿進於青紫,皇上特簡不次超遷,恩如此深重,焉敢不盡忠盡職繼之以死!今蒙皇上盛讚金獎,仰視高深捫心俯愧,請皇上暫收考語,留作臣進步餘地。」說完,已經完全平靜下來。
「嗯。你這個話也是題中應有之義。」乾隆也覺得自己前頭的話沒有留出餘地,笑道,「要是直不辭,也就不是錢灃了。當日勒爾謹、王亶事發,一案株連府縣吏死了七十餘人,錢灃同陝西巡畢沅曾兩次署理陝甘總督,也有奏疏彈劾。嗯——他奏摺里怎麼寫來?」他突然問紀昀道。
紀昀被問得一怔,這已經是幾年前的事了,時過境遷,每天不知看多奏摺文卷,冷丁地問出來,如何能夠記憶?但乾隆披閱的奏章他讀得多了,時有勒過紅杠下筆痛斥的,有用指甲掐出痕跡的是他在心留意之,有的連連勾圈,皆是他心悅嘉賞的字句……循這個道兒理清思路,一時就有了。紀昀仰著臉獃想一陣,笑道:「日子久了,臣不能全憶,只記得幾句警之言,『冒賑折捐,固由亶骩法。但亶為布政使時,沅兩署總督。近在同城,豈無聞見?使沅早發其,則播惡不至如此之甚;即陷於刑辟者,亦不至如此之多!臣不敢謂其利令智昏,甘所餌,惟是瞻徇回護,不肯舉發,甚非大臣居心之道……』別的臣不能背誦了。」
「這就是春秋責備,仁者誅心之論,」乾隆說道,「所以國泰的案子不能再拖下去,因緣瞻徇,不知還會有多員陷溺進去,跟著國泰倒霉。今日就下旨,劉墉為欽差正役、和珅為副,與錢灃三人趕赴山東,徹查此案。」
「是!」三人一齊離座叩頭,「臣等領旨!」
乾隆沒有他們起來,目中餘瞭了于敏中和紀昀一下,注視著三人說道:「國泰不同於高恆、王亶,真正是樹大深。他父子兩個連任封疆,父親文綬門生故吏周遍天下,中朝外居要津的很多,一案牽全局,辦理不善,不單是山東一省局面的事,波及大局就不好了。所以一要快,二要謹慎,蔓生枝節的事可以存疑,留待日後逐一去辦。如果此案中人事與你們幾人誰有瓜葛,就在這裡說明了,你們都是朕的肱信用大臣,也無需迴避的。」他像是要留給眾人思索餘地,挪著發酸的下炕來,出去「更」了。
和珅心裡一陣慌,他現在吳氏房裡放著幾十萬的寶房產就是國泰送來的供獻!要不要當「瓜葛」認承出去?——無需迴避——話是這麼說,一口就供出這麼多,國泰憑什麼送你這麼厚的禮?總得說明白吧?說得清楚嗎?當日鄂爾善收兩萬銀子,乾隆也曾說過「信任」鄂爾善,招出來沒事,認了供,不但兵部尚書撤了,接著大臣們一個會議讞審,定了斬立決,「從寬恩減」了仍舊是賜自盡!再說,遲不說早不說,特特地乾隆問出來才繳,你和珅算怎麼回事兒?崇文門稅關是天下有名的缺,你在任外能收這麼多錢,任呢?今年你收了這麼多,去年呢?前年呢?……聯想下去乾脆是不能想!和珅想到這裡也就不想了,總之是萬萬不能說,沒沒梢的事就像男合,按不住屁不認賬,蹬上子也不認賬!這麼著思量,他的膽氣立刻豪壯起來,竟認真審量起壁上的字畫來。一時乾隆回來,洗了手仍復升炕,于敏中在旁躬說道:「萬歲,錢灃在奏疏里劾奏的還有於易簡。於易簡是臣的堂弟,乾隆三十年放缺山東布政使。前次皇上召見,臣已經向皇上明白直奏。現在既查他的案子,臣還是該引嫌迴避。」
猜你喜歡
-
連載350 章
我本陷陣一小兵
便宜老丈人呂布屢次三番想把青梅竹馬的玲妹妹送去當王妃,怎麼辦?線上等,很急!
48.6萬字8 609 -
完結677 章

大唐盜帥
盜帥楚留香的隔代弟子杜長天無意間觸動了中華瑰寶「傳國玉璽」的神秘力量,致使穿越到了大唐王朝,來到了貞觀年間,且成為了名相杜如晦的兒子。在這史上最繁華的時代,杜長天憑藉後世知識創辦新式馬球、舉辦運動會,發明了一些古怪稀奇的東西。他寫一手好字,被人尊為書法大師,一字千金;背了幾首情詩,被人贊稱風流才子。作為穿越大軍的一員,集王侯將相於一身,以獨特的方式鑄就了一座輝煌的大唐王朝。
178.3萬字8 23678 -
連載65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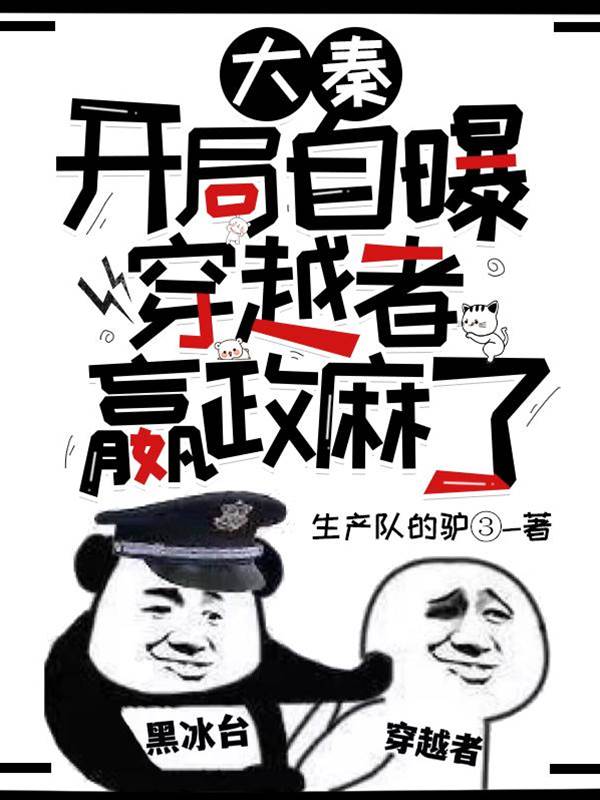
大秦:開局自曝穿越者,嬴政麻了
始皇帝三十二年。 千古一帝秦始皇第四次出巡,途经代郡左近。 闻听有豪强广聚钱粮,私铸刀兵,意图不轨,下令黑冰台派人彻查。 陈庆无奈之下,自曝穿越者身份,被刀剑架在脖子上押赴咸阳宫。 祖龙:寡人横扫六国,威加海内,尓安敢作乱犯上? 陈庆:陛下,我没想造反呀! 祖龙:那你积攒钱粮刀兵是为何? 陈庆:小民起码没想要造您的反。 祖龙:???你是说……不可能!就算没有寡人,还有扶苏! 陈庆:要是扶苏殿下没当皇帝呢? 祖龙:无论谁当这一国之君,大秦内有贤臣,外有良将,江山自然稳如泰山! 陈庆:要是您的贤臣和内侍勾结皇子造反呢? 祖龙:……谁干的?!我不管,只要是寡人的子孙在位,天下始终是大秦的! 陈庆:陛下,您的好大儿三年就把天下丢了。 祖龙:你你你……! 嬴政整个人都麻了!
127.7萬字8 7333 -
連載784 章
天下的一切都是朕的
我爹上馬是帝國龍帥,下馬是當朝丞相,人們稱呼我為小相爺。 我們爺倆都怕被朝廷當豬宰了,便奉行著猥瑣發育別浪的原則。 可我越藏拙,我這該死的才華就越是發光。 我越是躲,我這要命的魅力反而光芒四射。 我降智裝笨,一不小心就變得富可敵國。 朝廷警惕了,皇帝懷疑了,於是我坑爹了! 帝國的掌權者們要奪走我的一切,真的要把我們當成養肥的豬給宰了。 好吧,那就站起來,摘下面具,亮出獠牙。 不裝了。 我要讓這天下,變成朕的!
142.1萬字8 5650 -
完結936 章

大唐:開局娶了長樂公主
穿越到大唐,楊飛靠著祖輩留下財產,日子過得非常滋潤。一日郊游,救下一名少女,對方竟然要以身相許并當晚成親。沒想到洞房花燭夜剛過,岳父就帶大軍殺到,少女竟然是當朝嫡公主,岳父赫然是李世民!無奈成為駙馬,只能搬去長安城一起生活。從此之后,大唐變了一個樣。李世民:“賢婿,想當皇上嗎?我禪位給你啊。”蠻夷異族:“只要大唐有楊殺神在,吾等無條件俯首稱臣。”
182萬字8 33179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