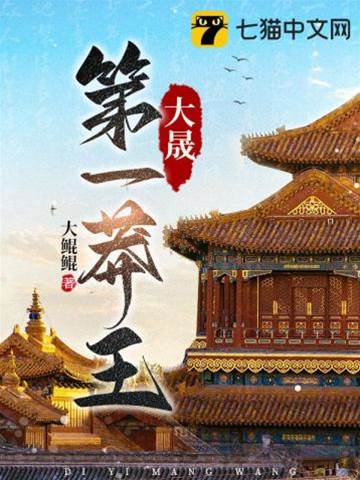《乾隆皇帝——雲暗鳳闕》第十七回 黃花鎮師生同遭變 狠親舅結夥賣親甥
顒琰和王爾烈在東屋安置下來。「在家靠娘,出門靠牆」,顒琰的鋪蓋自然設在東壁下。進門一張床是王爾烈住。這屋子既小,兩張床夾著一張桌子還有一把老梨木椅子,只剩下窄窄一條轉側之地。王爾烈船下步行半日,腳有點累,但暈船的病卻好了,神煥發映得臉泛紅,靠牆坐在床上,就著油燈凝神看書。一轉眼見顒琰雙手捧著茶杯皺眉沉思,笑道:「十五爺,人說你端謹木訥。我看不是的了——東宮裡師傅十幾個,侍講二十幾個,阿哥宗室子弟二十幾個,日日在一,看誰都一樣——這次出差跟您幾天,覺得和宮裡看脾舉止都有不同。您才氣斂,只是個名山收藏,半點也不木訥。」
「是麼!你看著書想這個,是一心以為鴻鵠之將至了。」顒琰一笑,目熠然一閃,但也只是一閃而已,隨即又變得恬淡自若,「公事公辦出不來際遇。毓慶宮裡規矩大,就是師生朝夕相,讀書作文之外揖讓禮見而已,不能見真,那就白頭如新。」[1]
他平素並不悉這個王爾烈,毓慶宮是康熙年太子讀書所在,自經雍正朝之後,規矩越來越大,尺寸進退都有制度,總師傅(太傅)、傅、侍講、侍讀層層的流當值,見面唯唯循禮如對大賓,退如游魚相忘江湖。王爾烈也只是「知有其人」而已,只覺得他是個端學書生罷了,出京這些日子,頭兩天生,後來王爾烈暈船,水米不進昏得毫無神,只是這半天同道,才算是有了點際遇。他原是覺得王爾烈有點木訥,聽王爾烈說他「木訥」,這份爽直也使他好。然他畢竟是個深沉人,天生年老,不願過多流親近,因道:「下船半日,炎涼世界判若天壤啊!一路見到那些兒話連篇,比照一下這百里荒地,怎麼人不慨?和珅還要在德州大興土木花天酒地地鬧!你今晚用我名義寫信給劉墉,他這個正欽差是幹什麼吃的?由著和珅胡折騰!」
Advertisement
王爾烈放下了書,見桌上現的瓦硯,倒了茶水橐橐磨墨,沉思著說道:「十五爺,彼也一欽差此也一欽差,寫信申斥恐怕於禮不合。和珅新學晚進第一次奉旨辦差,無論心地如何,沒有劉墉首肯,他不敢胡為的,左右我們就要和他們會面,聽一聽他們意見再說話不遲。依著我的見識,先給皇上發一份請安摺子,把眼前形奏知聖聽,連那份啟事也寫錄進去。我們到德州,皇上的批文也回來了。只是這要十五爺親自繕折才。我給您磨墨鋪紙就。」
「你說的是。就是這樣的好。」顒琰說著就坐了椅上,見那筆禿不中用,喊了王小悟過來,把搭褳里的筆和請安摺子取出來。他素尚儉約,見那摺子紅綾封面燙金邊,躊躇了一下道:「就用這素紙,隨分常,皇阿瑪不至於見罪的——小悟去吧——」他沉著緩緩濡筆,慢吞吞道:「這份請安摺子可以寫給老佛爺和皇后……王師傅,我總覺得有許多話要建議,這一大片鹽鹼地老在眼前晃,種作糧食,或者真的仍舊滿地黃花。那該多好!可又理不出頭緒從哪講起。」王爾烈不心下一陣,諸阿哥中他最看重的是八阿哥顒璇,出口章才氣橫溢,為人事落落大方,且沒有一紈袴習氣。這裡一比,反覺顒琰務實坦誠,關心民瘼出於至,和自己更近了些。頓了一下,王爾烈道:「我一路也在想這件事。運河這一段是南高北低,想放掉大浪淀的鹼水非從青縣北決渠運不可。若要治,須得把大浪淀和堤外渠通連了,由滄縣從運河放水,到青縣鹼水運,把外邊的水變引渠變活水,這就不是一縣之力能辦得到的。青縣現歸天津道,滄縣又是滄州府治區。要辦這件事,頭一條要把青縣劃歸滄州府轄理。」顒琰聽得目炯炯,說道:「是!我心裡模模糊糊的,不知這事誰來管。這就明白了。可以請旨把青縣撥歸滄州府,事權就統一了。」
Advertisement
王爾烈見顒琰躍躍試提筆要寫,一笑又道:「十五爺,還有更難的。我方才說的,其實是把這段運河分流為二。水勢一分,運河舟楫航運就是個事。滄縣再向南到德州這段運河要多注水。才能供得上這邊的分流使用,因此上游運河要疏浚加寬。青縣下游鹼水回運,下游原來的河道要清淤,要加固堤岸。這是多大的工程?要花多銀子?又由誰來統籌治理?我們不懂水利,這要請旨,派能員幹吏和河工上通水利的員實地踏勘。總之既不能阻斷運河漕運,又把這段地用活水沖洗了,才是上善之策。」顒琰放下了筆也陷沉思,良久,笑道:「興一利好難!你一邊說我就在想,裡邊這道引渠可以由府縣自籌工銀。荒地治理出好田,我看百萬畝地是有的,一畝地按七兩賣,有七八百萬的銀子收項,連運河疏浚的銀子都有餘,只是一時要朝廷這麼多錢,到部里要生出議論的。再說要像魯老漢說的那樣年年洗地,年年施,也實在太麻煩了。」王爾烈笑道:「這個不必慮。我方才說的是『治』。只要有活水常流,深挖排鹼,鹼花泛不上來,也就不是鹽鹼地了。真能照這樣治理起來,這裡雙季稻都能種,十年之後十五爺再來看,準是魚米之鄉!」
「我這就寫!」顒琰被他說得興起來,一雙眸子閃爍生,「這樣的好事,正是萬世之利。我看是這樣,拿得定的寫條陳,拿不定的建議皇上下部勘議集思廣益。這樣施為起來,算我出京辦的第一件事呢。我寫后你再潤——王小悟去前街把那張啟事揭回來,奏摺附帶,啟示算夾片一併送進去。」王爾烈也不言聲,側坐在床頭,提起那支禿筆,他也真箇好記,筆走龍蛇頃刻之間已將啟事背錄出來。顒琰驚異地看了他一眼,沒有說什麼,就硯中提起筆來……
Advertisement
外面的風似乎更加狂烈,發著裂帛撕布一樣的尖嘯,又像猿啼狼嚎遠遠傳來,從屋上掠頂而過。窗紙時而了驚似的一陣慄,一鼓一癟掀著,不知是雪粒還是砂石,擊在窗欞上,打在門板上,一片聲沙沙作響。這座小小屋宇不知歷了多年頭,似乎經不起這風力肆,吱吱咯咯響著**。風大氣寒的臘月天,炭盆子火焰也不旺,紅中泛黃,像將死迴返照的人臉那樣詭異難看。顒琰寫得專註,勘勘收筆才覺得沁涼骨的冷,剛要王小悟過來添炭,卻見人子拉了風門進來,便道:「冷得很,這裡加點炭,你們兩屋也收拾暖和一點——你神不對,出了什麼事麼?」
「沒什麼。」人子道,「聽見北院西廂里有人商量辦壞事,來問問爺,咱們管不管。」
顒琰和王爾烈目霍然一跳,顒琰一手抓著椅背,臉已變得蒼白,王爾烈問道:「是黑店?是有賊?」
「爺們不要慌。」人子道,「那屋裡是幾個人販子。他們商量在這裡買來的十幾個姑娘要賣到廣里。說有個威爾遜的英國片商出大價錢買,還說先哄著們到廣州,再倒手一個能賺兩千兩。嘁嘁嚓嚓商量著,我都聽了來,還要稟爺,魯老漢一家恁麼善,舅舅竟不是個人,人販子里也有他!幾個人販子笑話他『外甥外甥都敢賣,謹防魯小惠娘知道了一剪刀喳死你個狗東西』,他還笑,說『我姐病得七死八活不能,怎麼能知道?要知道我送兒子去跟洋人當跟班,兒穿綾裹緞當姨太太,謝我還謝不及呢!』這個畜牲,我聽著恨得牙,一掌劈了這狗日的!」
「清平世界居然有這樣的事!」顒琰蒼白的面孔一下子漲得通紅,一撐子站起來,「前街住的都是滄州的衙役,帶我的名刺,他們主事的一給我拿下!」王爾烈道:「這事容易,我出面去辦!」人子道:「不。裡頭還有一個師爺,我聽他說話口氣是滄州府衙的,來這裡指揮關防。一口一個『我們府尊』,又說『縣裡也要打點』,他們都是一氣的,前街衙役有一百多,店都住滿了,聲張起來反咬我們一口,現虧就吃定了!」
Advertisement
王爾烈和顒琰不面面相覷。府和人販子合夥販人,這太駭人聽聞了!一時屋裡靜下來,呼呼風聲中燈花「剝」地一,竟驚得顒琰一起栗!許久,王爾烈才道:「我們只有四個人,十五爺份貴重,白龍魚服,不能冒這險。王小悟去欽差座艦,發諭滄州知府、滄縣縣令到船上參謁,會同來黃花鎮當面料理,十五爺看這麼著可行?」
「不行。」顒琰冷冷說道,「難保他們就是一夥子蟊賊。也許府縣令現在就在黃花鎮!我們一傳知,下頭串供了,反倒落個捕風捉影的名聲兒!這樣,現在不要,暗地裡線上他們。他們賣人,總要上船到德州,途中攔截了一網打盡,嚴刑審明了連拔掉,刑部置。」人子道:「照常理該這樣的,我聽魯惠兒的舅說,『行李快上船,後來夜風大天冷,要弄暖一點,凍病一個路上沒法張羅。』——看樣子他們立馬要走!」顒琰驚訝地說道:「我們晚飯在魯家。惠兒兄妹還不像要的樣子呀!」
王爾烈道:「起王小悟,在魯家門口守著,有什麼靜報過來再說。」人子道:「我方才已經到北院走了一遭,人都沒睡,十幾個姑娘都在北屋正堂有說有笑,們還以為到德州山陝會館去打雜工掙錢。我王小悟到魯家守著,我守後半夜,看孫子們有什麼作。他這會子已經在那裡了。」
正說著,便聽外頭風地里腳步聲,王小悟一頭闖了進來。他裹一老羊皮袍,猶自凍得紅頭蘿蔔似的,又吸溜鼻子又打噴嚏,一進門就說:「任爺真是**湖,料事如神!魯惠兒那狗日的舅舅真的去了,敲門著『天、惠兒預備行李上船』我就趕回來了。我的爺,真沒見過這個,天理王法人都沒有!這世道日娘的怎麼這麼黑,老北風也沒這門涼!」
「殺人可恕,理難容!」顒琰一擊案咬著牙道。剎那間王爾烈覺得他的冷峻中帶著異樣的兇狠猙獰,未及說話,顒琰已在披斗篷,「走,瞧瞧去!」
外邊果然又黑又冷。似乎是零星雪,夾著沙粒隨風裹著,打在臉上鑽進脖子里冰涼生痛,雖然都是重裘厚袍,心都像被冷氣浸了,覺得紙一樣薄,出錢記客棧好遠,王爾烈和顒琰眼睛才適應了那黑暗,見大地泛著淡青的雪,才知道雪已經下了有一陣時辰了。此時正是更深子夜,連前街的燈火都撤了,寂寥空曠的街衢只能約聽見老遠「梆梆梆——柝柝柝」的打更聲,隔著風時斷時續傳來。正走著,從巷子口黑地里「呼」地竄出一個影子,一躍人來高,像是一條野狗的模樣,直撲向顒琰!顒琰一個乍驚,揚起右手護臉,道:「狗!狗!」趔趄一步幾乎摔倒在地。那畜牲正要再撲,走在前邊的人子倏地回,也沒有什麼花哨張致作,無聲空劈了一掌,那狗哼也沒哼就倒在地不了。顒琰余驚未息,連連問:「是狼是狗?是狼是狗?」
「是狼。」人子道,「是條極了的狼。逮住什麼撕咬一口算一口,沒傷著主子罷?」「沒有。」顒琰抖著聲氣說道,「只是唬得我幾乎走了真魂——這畜牲忒膽大,我走在裡邊,它隔著王師傅來咬我!」王爾烈道:「狼這種東西專咬膽小的。我有家鄉秋糧上場,全家老小天守場,大人睡外邊,孩子睡人圈兒里。」「野狼總是跳進圈子裡頭傷人——今晚沒有人子,我這罪就百莫贖了!虧了你好手段——我這會兒腳都是的呢!」人子笑道:「我也不防鎮子里還鑽進了狼!主子一頓五斤喂著我,傷一汗我也是擔不起的。」
猜你喜歡
-
連載337 章

大明妖孽
一名執拗的公差,昨日還被誣陷為十惡不赦的「兇徒」,今天卻化作了反腐的「利劍」。一個不善持家的二世主,三月前還在為生計一籌莫展,三月後卻成了拯救萬民的「大羅神仙」。一位心狠手辣的邊關名將,大獲全勝反被革職查辦,肆意妄為卻得到貴胄的垂青,王孫的美言……屠刀下,良知如芻狗般獻祭於天!一幕幕「喜劇」正在激情的上演!地獄裡,惡鬼悠閑地打著算盤;登記蒼生的孽債;也憧憬著何時重返人間……
90.3萬字8 591 -
連載2238 章
諜云重重
當發現自己雙手沾滿了鮮血,怎麼辦,在線急!當發現自己前身是一個絕對的極品渣人,怎麼辦,還是急!這是一個自我救贖,一個游走在灰色邊緣的人進行的救贖。…
449.7萬字8 5917 -
連載1089 章

我在明末當太子
崇禎十七年,三月十六日。李自成兵攻陷居庸關!兵鋒直指北京城!整個北京城,人心惶惶。而就在這人心惶惶的時候。來自二十一世紀的朱慈烺穿越而來!面對糜爛的局勢,面對眼前人心浮動的官兵,百姓。朱慈烺一陣無力,就在這危急關頭!神級選擇系統開啟!開局獲得新手大禮包,獎勵五百頂級錦衣衛侍從!看著面前即將崩壞的局勢,還有三天的時間!唯有,殺!以殺治天下!殺貪官!殺污吏!五百錦衣衛,抄家滅門!三天時間,守住北京!
193.4萬字8 14952 -
連載34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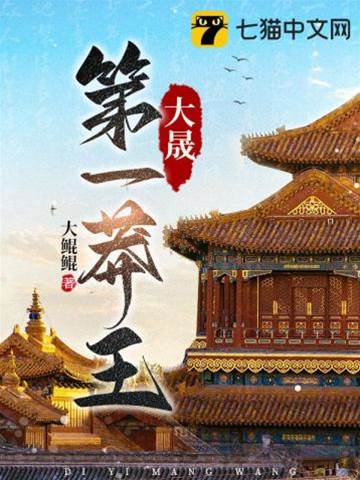
大晟第一莽王
醒掌天下權,醉臥美人膝。這句話,差不多是所有男人共同的追求。但項庭,卻偶然得到了實踐的機會!魂穿大晟,他成為了越王世子。坐擁美女萬千,執掌權柄無算。一言而決萬人生死,一言以定九鼎乾坤!…
61.3萬字8 1425 -
連載829 章

大宋文魁
青州古城小老板張唐卿,穿越到了宋仁宗時期,這個時期群星璀璨。范仲淹、歐陽修、韓琦、包拯、狄青等等一系列大人物粉墨登場。且看張唐卿如何玩轉大宋,如何成為最閃亮的大宋文魁,如何帶領大宋走上富、強之路。
144萬字8 16996 -
連載897 章

玄德
在你面前的是!漢室宗親、孝景皇帝之后、涿縣街頭霸王、海內大儒盧植親傳弟子、東漢浪漫主義詩人、雒陽紙貴直接責任者、古文經學派辯經達人、古文經學派少壯派領袖、《左氏
224.5萬字8 973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