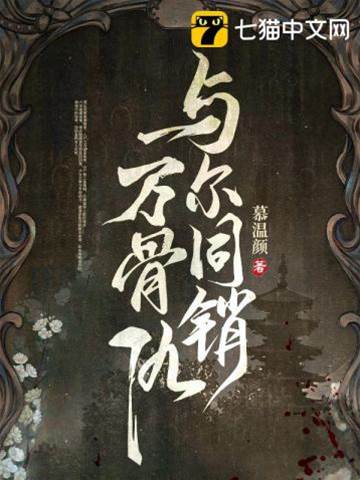《重生之庶女歸來》 第139章 傷心人在天涯
「你,中毒了?」何當歸謹慎地打量著坐在影中的孟瑄,問,「嚴重嗎?」
孟瑄輕點了一下頭:「還好,就是走不了路了。」
何當歸歪了下腦袋:「走不了路了?那你怎麼跑到桃夭院來的?」
「費了點兒事。」孟瑄晦地答道。事實上他費的勁兒實在不小,先設法說通了父親讓自己在羅府留宿,又等欣榮殿的眾人走了之後,悄悄地跟在彭漸他們幾人的後面……倒立著用雙手「走」過來的。
何當歸致歉道:「瑄公子,我不知你也有力,因此把『茶』直接加在了茶壺中,實在抱歉。其實你中的這種『茶』不是毒藥,而是一種專門用在習武之人上的麻醉藥,我也沒有辦法幫你解,只能等藥自己褪去,勞煩你將就個兩三天吧。」其實不獨他一人,當時大殿之上所有聞過香味的人都中了這種麻醉藥,不過只有茶案旁邊,過茶水的四人藥被催化開了而已。
彼時,用銀針封了自己的中府,沒有吸那道香;而老太太沒有力,不影響;麻醉藥瞄準的目標人,那個面刺客,業已經嘗到了苦頭,用了急保命之法才暫時擺了藥;可自己倒是小看了這個孟瑄,沒想到他的力也深厚到會被安息草牽制的地步。因為記得書上曾說,只有功力在一甲子以上的習武者,吸安息草之後才會有麻痹癥狀,癥狀的表現況因人而異,有全麻痹者亦有半麻痹者。事實上,何當歸覺得自己的功力也肯定到不了一個甲子,不會安息草的影響,用銀針給自己封只是以防萬一。
「將就?」孟瑄劍眉一掀,「你的意思是,我未來的三天里都不能走路了?」
Advertisement
何當歸點了下頭,只覺得頭暈得,腰間的帶脈被一道道的真氣堵塞得非常難,唉,沒想到已經回到自己的房間了,還是不能安靜地休息……天大地大,難道不能有一個讓自己默默治癒傷口的角落嗎?賭氣地看了對方一眼,反正是個小孩子,管他的呢,於是在對方略驚詫的目中解去披風,又下外丟在地上,像一個患了腰痛癥的老太太一樣艱難地爬上了床,扯過被子將自己裹一個蠶蛹。
太好了,有了繭了,躲在這裡面,再沒有人能傷害。
孟瑄敏銳地察覺到,這丫頭不像晚上宴會時那樣輕快自在了,這才是真實的嗎?還是被那個人擄去的時候了傷,所以難到不耐煩應付自己?沉默了片刻,孟瑄問:「那人傷到你了嗎?我略懂……用力為別人療傷的方法,我可以幫你治傷。」
何當歸悶在被子里不想說話,不管是外傷、傷還是心傷都隨它去吧,時間久了總會好的,現在需要的是一個安靜而不打擾的角落。自己的逐客令這樣明顯,那傢伙看不出來麼?
得不到迴音的孟瑄索也陷了沉默,一邊繼續嘗試運功出麻藥,一邊想著自己的心事。
此次揚州之行,真是一波三折險象環生,先是在兔兒鎮救下了素瀟瀟,後來又被錦衛的英人幾次三番的追殺,幸好在自己傷重失的危急時刻,遇到了一個善心的小道姑懷弈,不只為自己包紮了傷口,還將的給自己穿,若不是,只怕自己又要重新投一次胎去了。
那一日和的同伴走了之後,自己先吃下了餵給自己的止草藥,又生吃了留給自己的那幾隻鳥蛋,覺恢復了一些力氣,才在那座山上覓到了一個安全的療傷所在,一直等錦衛搜山的人走了幾天後才出來。第一件事就是找到了那座山上唯一的道觀水商觀,打聽法名中有「弈」字的師傅,最後找到了那位小道姑懷奕。
Advertisement
令人難過的是,已經完全不記得他了。細問之下他才知道,原來那一日救完了他之後,與同伴一起回道觀的時候遇到了山中的野,二人雙雙跌落懸崖。跟一起的那個道姑當場被摔死,雖然幸運地撿回一條命,可是卻撞到了頭部,失去了很多的記憶,包括曾經救過他的這一部分。
不過當他拿出那套救命恩人的小時,立刻就認出了那是的,再加上在道觀的葯廬做事,諳藥理,並且經常在這座山上採藥,與那一日救自己的那個穿道袍的子況都相符,所以他很肯定懷奕就是自己要找的人。
這懷奕不但救了自己命,而且失憶和失去摯友的事他也有責任,再加上自己曾穿過的,於於理都要對負起責任和還報恩。因此,他問可願還俗,跟他一起離開道觀,重紅塵。開始是猶豫的,不過自己鄭重承諾了將會照顧一輩子,於是答應還俗並跟他回家。
後來到了揚州,他聽說那個未來的「天下第一酷吏」耿炳秀要來理一樁知州貪污案,即將到達揚州,那等惡賊決不能放過,於是他讓家僕將還俗之後取名為「紫霄」的懷奕先送回京城孟府。
他問過紫霄的世,得知是一位家道中落的大戶之,只因不願在親戚的家中過寄人籬下的屈辱生活,才毅然決然地上水商觀出了家。
他思忖道,自己既然將恩人接出了道觀,必然要給一個名分,讓可以在孟府過得好一些。若是讓半主半仆的住進孟府,一日兩日里還可以告訴眾人說,是他的救命恩人;日久天長下來,沒有一個講得出口的份,難免會被府中之人欺侮。只是的出過低,做不得他的夫人,因此他就讓家僕先以「姨娘」的名義將安置在自己的廬風園,也好讓住得安心。
Advertisement
反正家裡的六個兄長都已有了妾室,母親也曾往自己房中放過三個通房丫頭,只是自己不想瞧見那三個人日里爭風吃醋勾心鬥角慕虛榮的模樣,索一起打發走了。如今他從外面帶回去一個妾也不算逾矩,紫霄出於道觀,也算是世清白,再加上曾救過自己命,相信母親也會對滿意並善待的。
而素瀟瀟是天字第一號欽犯胡惟庸的養,不能往家裡放,可是自己前世的朋友,實不忍看繼續流落江湖,賣藝為生。在他看來,子無論是格堅強的,還是懷武藝的,本質上仍然是易傷的,因此保護子是男子的天職。
儘管素瀟瀟獲救之後,看向自己的眼神中滿是驚艷和傾慕,儘管自己對並無男之——事實上,前世十九年加上今世的十一年裡,他還從未對哪個子過,大概他天生就是個無之人吧——儘管前世一個把酒言歡、縱論古今的朋友用那樣的眼神瞧著他,未免讓他覺極不自在,不過他還是託了陸風鏢局將送去京城,暫且安頓在自己的別院。只希能儘快依著前世的軌跡,遇見那個「羅白及」的男子並上他,那樣自己就可以而退,祝福他們了。
此次揚州之行,不知不覺中撿回了一恩人一故友的兩個子,為何好像還是點什麼似的……是因為刺殺耿炳秀失敗嗎?那個耿炳秀中了自己的長風訣,應該跑不遠才對,為何連日里自己明察暗訪都沒有他的一消息呢?蟄伏在揚州的錦衛據點的房頂上,聽了很久,也沒聽哪個人提過耿炳秀去了哪兒。
話說回來,他原以為憑自己的小孩子,大約是打不過那個賊的,因此約戰之前特意去選了一塊對自己最有利的地勢,還以襲的方式出場,算是下棋之中下了個先手。沒想到那廝的武功,並不像前世里自己從旁人聽來的那般高不可及,是如今的耿炳秀功力尚未大,還是那一日他對著自己時掉以輕心,沒有拿出真正手段來呢?可惡,上次那樣好的機會都沒能殺死耿炳秀,若從今往後他有了戒備之心,都不落單,出門時都帶著陸江北那一伙人的話,那再想刺殺他就難了。
Advertisement
不如明天去向父親告一個假,就說……就說自己對柏煬柏的授課也嚮往不已,因此想留在澄煦書院讀幾個月的書再回軍中。一來現在沒有戰事,在軍中除了點卯就是習武,沒甚要的;二來他自小不讀書,畢竟前世最慣讀的是《六韜》和《鬼谷子》,今世實在不想搖頭晃腦地去誦《三字經》和《百家姓》,若是父親聽聞自己主要求讀書,他定然會欣然應允的。
好,就這麼辦!相信耿炳秀那廝如今還在揚州,而且正藏在什麼地方療傷和練功,這次是殺死他的千載良機,錯過這一次,以後自己即使功力恢復到上一世的全盛時期,也不可能單挑錦衛那一撥人,「咳咳……」床上子的輕咳聲打斷了他的思緒,讓他反應過來,他不是在自己的南苑客房中默想心事,謀劃鋤之計,而是在一間睡著一位不太友好的小佳人的閨閣繡房之中做客,而且原因是因為——他看向床上包裹嚴實的佳人,出聲詢問:「喂,何小姐,為什麼我運功麻藥了這麼久都不起一點作用?你這麻藥哪裡弄來的?真的要等上三天才能恢復正常嗎?」
「……」
「喂,你睡著了嗎,丫頭?」
「……」
「你不舒服嗎?有什麼我能幫忙的地方嗎?你要看大夫嗎?我把你的丫鬟和你家裡的人來吧?」
「別人,你出去就行了。」
「……我也知道半夜三更跑到你的房裡來是於禮不合,可一來我的迷藥是你下的,你就要對我負責;二來我就是想回也回不去了啊——我聽說你們羅府的東西大院之間有隔牆,每日子時一刻就要上鎖,現在是子時三刻,你們羅府給我安排的的客房在牆的那邊,如今我又行不便,所以不是我賴著不走,而是我確實是有房回不得啊。」孟瑄搖頭嘆氣。
何當歸咬牙切齒:「桃夭院里到都是房間,你願意睡哪一間就去睡哪一間好了,若是讓我再聽見你唧唧歪歪,我一掌拍死你扔去喂野貓和野豬。」聽得桌子那邊沒了回話的聲音,何當歸心中暗暗欣,對付那些皮孩子,打不管用罵不管用,最管用的一招就是恐嚇。
覺房間清凈下來,本應好好休息上一回的卻難以眠,平生從未害怕過黑夜的,頭一次覺得今晚的夜黑的讓人發抖,打了個寒,在棉被中一片秋天的枯葉……一定要咬牙過去,不管重來幾次,只要有得選擇,都不會選擇去喝那一碗孟婆湯,因為,在這個世人都「失去了記憶」的世間清醒而痛楚的活著,是自己的選擇,也是一個人的征途……當歸,只要咬咬牙,你一定可以過去的,「那我就不客氣的選這一間啦。」一個聲音著何當歸的後腦勺響起,徐徐的熱氣拂上的耳畔,「喂,被子分我一半,謝謝。」
抖了一下猛然轉頭,不可置信地瞪著不問自取,擅自分去自己一半枕頭的那張燦爛笑臉,雖然想把對方踹下去,可是子卻已經虛到極致,做什麼的力氣都沒有。沒想到保定伯孟善堂堂亞聖孟子的傳人,竟然教出一個如此金玉其表,敗絮其中的登徒子兒子,才十一歲就鑽子閨房,爬子綉床!
何當歸怒極反笑道:「瑄小公子,實不相瞞小子今年年方十歲,貌若無鹽,骨瘦如柴,你若想香竊玉應該去找我的好二姐才對,我們全家都會歡迎你的。」
「你的床上怎麼只一個枕頭一張被子,我家裡我的床上有四個枕頭兩床被褥呢。」孟瑄用手指揪著被頭,想把那條裹得像蠶繭一樣的被子剝開分一杯羹,同時教育小丫頭說,「以後你睡覺應該在床上多放幾床被子,睡起來又暖和又熱鬧,這樣你就不用一個人孤零零發抖了。」剝了很久,每次拽開一點就被對方重新收,孟瑄無奈道,「我是看你被那大惡人捉去一次,嚇得晚上睡覺直發抖,才好心來看看你的,你好歹掀開讓我看看你嘛,你到底哪裡不舒服?我會治病。」
猜你喜歡
-
完結1962 章

腹黑狂妃︰絕色大小姐
殺手?特工?天才?她都不是,她是笑顏如花、腹黑兇猛、狡猾如狐的蘭府家主。 想毀她清白的,被剁掉小指扔出去喂狗;想霸她家業的,被逼死在宗廟大殿;想黑她名節,讓她嫁不出去? sorry,她一不小心搞定了權傾天下、酷炫狂霸拽的攝政王大人! 他︰“夫人,外面盛傳我懼內!” 她眨巴眨巴眼楮,一臉無辜︰“哪個不長眼的亂嚼舌根,拉出去砍了!” 他︰“我!” 她︰“……”
180.4萬字8.09 132089 -
完結137 章

招魂
-落魄的閨閣小姐X死去的少年將軍-從五陵年少到叛國佞臣,徐鶴雪一生之罪惡罄竹難書。即便他已服罪身死十五年,大齊市井之間也仍有人談論他的舊聞,唾棄他的惡行。倪素從沒想過,徐鶴雪死去的第十五年,她會在茫茫雪野裡遇見他。沒有傳聞中那般凶神惡煞,更不是身長數丈,青面獠牙。他身上穿著她方才燒成灰燼的那件玄黑氅衣,提著一盞孤燈,風不動衣,雪不落肩,赤足走到她的面前:“你是誰?”倪素無數次後悔,如果早知那件衣裳是給徐鶴雪的,她一定不會燃起那盆火。可是後來,兄長失踪,宅田被佔,倪素跌落塵泥,最為狼狽不堪之時,身邊也只有孤魂徐鶴雪相伴。 伴她咬牙從泥濘里站起身,挺直腰,尋兄長,討公道。伴她雨雪,冬與春。倪素心願得償,與徐鶴雪分道揚鑣的那日,她身披嫁衣將要嫁給一位家世,姿儀,氣度都很好的求娶者。然而當夜,孤魂徐鶴雪坐在滿是霜華的樹蔭裡,看見那個一身紅的姑娘抱了滿懷的香燭不畏風雪跑來。“不成親了?”“要的。”徐鶴雪繃緊下頜,側過臉不欲再與她說話。然而樹下的姑娘仰望著他,沾了滿鬢雪水:“徐鶴雪,我有很多香燭,我可以養你很久,也不懼人鬼殊途,我們就如此一生,好不好?”——寒衣招魂,共我一生。 是救贖文,he。
50.1萬字8 22370 -
完結609 章
毒后歸來之鳳還朝
一朝錯愛,她為薄情郎擦劍指路,卻為他人做了嫁衣,落了個不得好死的下場。上蒼有眼,給了她一次重新開始的機會。這一次,有恩報恩,有仇報仇,她手持利刃,腳踏枯骨,鳳回天下。看慣了人們驚恐的目光,她本想孑然一生,卻陰差陽錯被個傻子絆住了腳步。這世上,竟真有不怕她的人?逆流而上,他不顧一切的握住了她的手。
153.9萬字8 14537 -
完結36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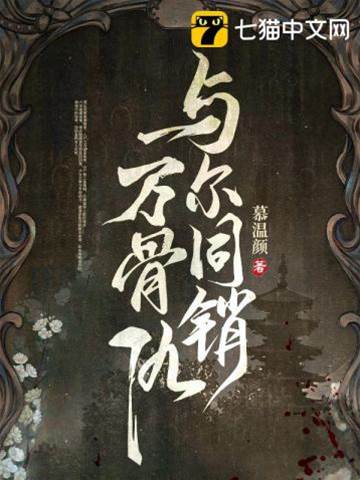
與爾同銷萬骨仇
深山荒野狐狸娶親,人屍之內竟是魚骨,女屍愛上盜墓賊,吊滿詭異人影的地宮...... 六宗詭譎命案,背後隱藏著更邪惡的陰謀。 少女天師與年輕尚書,循著陰陽異路解決命案,卻每每殊途同歸。 暗夜中的枯骨,你的悲鳴有人在聽。
32.6萬字8 7472 -
完結508 章

嫁給瘋批太子衝喜後
慕家不受寵的嫡女,被一道聖旨賜婚給命在旦夕的太子周璟沖喜。 不少人看笑話,可別把人給衝死在榻上。 周璟一睜眼,就多了個未婚妻。 小姑娘明明很怕他,卻還是忍不住的表忠心:“殿下,我會對你很好的。” “殿下,你去後我定多多燒紙錢,再爲您燒幾個美婢紙人。” “殿下,我會恪守婦道,日日緬懷亡夫!” 陰暗扭曲又裝病的瘋批周璟:…… 很久沒見上趕着找死的人了。 成親那天,鑼鼓喧天。 數百名刺客湧入隊伍,半柱香前還在裝模作樣咳血的太子劍氣淩厲,哪還有半點虛弱的樣子? 周璟提著沾血的劍,一步步走至嚇得花容失色的她跟前,擦去濺落她右側臉頰的血,低低似在為難:“哭什麽,是他們嚇著你了?”
84.6萬字8.18 13493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