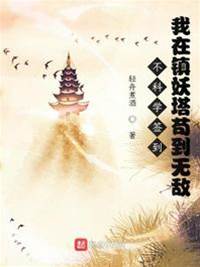《財神春花》 第 90 章 常鱗凡介
談東樵與韓抉此前已猜到了些由,但此刻細細讀完,仍不由得暗自心驚。
韓抉深吸了一口氣:“果真如子恕所說,我們一直對抗的妖尊,其實是個凡人?老談,你是如何猜到的?”
“與其說是凡人,倒不如說……是個二五子。”談東樵淡淡道。
“凡人食老五丹,雖然見,但并非沒有先例。斷妄司典籍中曾載有一例,人食老五后,雖得其妖力而用,但無法化用修行,亦不能羽化登仙,一半為人,一半為老五,若不繼續食用其他老五,其力終將衰竭,如普通凡人一般亡故。”
他轉步出墓室,韓抉連忙跟上。
“妖尊年年臘祭都要吞食老五作為祭品,又要混以尋、梁兩家的鮮。這儀式太邪,我便想起了典籍中看過的那一段記載。最初的聚金法陣以子恕為主陣法寶。子恕既亡,法陣難以為繼,錢仁記起子恕曾吞食錢家枕下財脈化為人,便去尋那財運深厚之人,挖了枕骨來做主陣的法寶。只可惜凡人財脈終有盡時,蘇玠在安樂壺中看見的許多枕骨,就是這些年來用盡而棄的。”
韓抉恍然大悟。
兩人登上涼池一側的一座高地。地半山,周圍的樹林均被砍伐干凈,舉目去,可以俯瞰整個汴陵城。
談東樵負手東,目悠遠落定在一,久久不。韓抉順著他的目看去,那方向正是吳王府。
韓抉嘆道:“你……怎忍心讓春花老板孤去見妖尊?”
“我贈予一,應當能護周全。”
韓抉搔搔頭,哦了一聲。忽覺不對:
“我最近沒做過什麼新法啊。你給春花老板準備了個什麼?”
談東樵沒有正面回應。
“是自己堅持要去。”
Advertisement
他黑眸微垂,神和:“并非庭中蕊,而是歷風的長帆,自有自己的主意。”
韓抉:“……”
他神凝重起來:“老談,你沒什麼經驗。但師弟我縱橫場這麼多年,像你這樣的狀況,我見多了。”
“哦?”
“你好像……被這個長孫春花給迷住了。”
談東樵有些意外地挑起眉:“如何算是被迷住了?”
“說的話,你都贊同,想做的事,你都全力支持。一提到,你就出這副……”韓抉盯著談東樵,眼睜睜著他角輕輕一勾,出前半輩子沒見過幾次的溫和笑意。
“……膩笑的模樣。”
“要說沒給你下過蠱,我是不信的。”
談東樵莞爾,半晌,斟酌著用詞,解釋道:“確實與別不同。但我和,并不是你想的那樣。”
韓抉翻了個白眼:“你廢話。我只問一句——”
“你們親過了沒有?”
“……”
談東樵怔住,難得地語塞了。
韓抉:“……”
“你…………你們……”
韓抉頭一次發覺皮子追不上腦子的轉速。他腦中霎那間冒出無數彩斑斕的畫面,幾乎要把腦子炸碎渣。
霖國夫人把京城佳麗踅了個遍,都沒找到一位談東樵能看得眼的。他那會兒怎麼說的?
我此生夙愿在于修道問心,守護天道,婚只會誤人終生。還請姨母將做的熱都放在韓抉上,定有斬獲。
著韓抉這三觀震碎的模樣,談東樵嘆了口氣,正道:
“我與,并無可能。心懷紅塵夢想,志氣頗高,需要的只是一個老實本分的贅婿。而我負重任,此已許社稷,再難許君。”
韓抉終于闔上張大的,頗有同地點點頭:
Advertisement
“也是,你家老太爺脾氣那樣古板,你若終不娶,他便當你獻社稷了,倒也沒什麼。但若是給個商戶做上門婿,他怕會拿刀剁了你。”
他描述得繪聲繪,談東樵有一瞬間的恍惚,仿佛祖父真的在他眼前然大怒。
他自覺有些好笑,搖了搖頭,拋卻這些陌生而毫無裨益的心思。
對長孫春花而言,嚴衍是個合適的人選,而談東樵卻不是。
對談東樵而言,長孫春花亦非世俗良緣。
他明白,也明白。
所以,他追問那晚馬車上發生的事,永遠問不清楚。
談東樵轉:“師弟,就依咱們之前商議之法,準備破陣吧。”
韓抉震驚:“現在麼?”
“聚金法陣日久年深,非靠天時不能破陣。春花自告勇去見妖尊,一則是放不下吳王世子,二則,也是為我們拖延時間。”
此刻春雨已霽,日照當空,談東樵舉目天:
“時辰已到,我去引汴陵江水陣缺。你與兄弟們布好天網,錢仁心魔深重,罪惡滔天,萬勿讓他逃。”
韓抉默了一默:“老談,你說的自然是正理。但你可知……汴陵一年向朝廷納多賦稅?”
“我已折回京,稟報陛下。”
“陛下同意了?”
談東樵靜了一瞬:“自然。”
韓抉見他如此篤定,便寬了心,拍拍口:“我還擔心陛下不肯呢。畢竟對朝廷來說,能上繳賦稅便行,管他是誰繳的呢?”
談東樵無聲一笑:“財帛鹽鐵是戶部所專,我所知不多。但……有人說了一句話,我深以為然。”
“什麼話?”
“說,汴陵的財脈,從來不在聚金法陣中,也不在高門大戶的家祠中,而在升斗小民的雙手中。百姓有信念,只要有奇思妙創,肯辛勤勞作,便一定能獲得財富,這才是真正的財脈。”
Advertisement
時已正午,鴛鴦湖畔滿了汴陵百姓,都在等待一場盛事——
汴陵江上的三月桃花汛。
汴陵江水源自昆侖,仲春時節,昆侖冰雪消融,春水大汛,行至鴛鴦湖口這一段,恰逢兩岸桃花盛開,灼灼其華,故稱桃花汛。
此刻,江面層層升高,水霧如煙,滴珠如寶,在正午暖的照耀下宛如無數冰凌,閃閃發。
汴陵人財求財,迷信一切與財運有關的東西。百姓們相信水便是財,桃花汛期,在江岸邊沾染一長雨,接下來的一年都會有好運氣。
當然,這不會影響他們起早貪黑地開門打烊,不會影響他們四方奔走采購最稀缺的貨品,更不會影響他們絞盡腦做出汴陵獨一份的手工。
但若一切順利,他們依然覺得,是那日沾了一桃花汛帶來的如意。
驀地,一個圍觀者驚起來:
“江心有人!”
一艘小葉般的畫舫孤單地漂在江心,舫頂的檐脊上,飄然立著一個人,青博帶,迎風獵獵。
湍急呼嘯的洪波自西向東,仿佛從天而降。巨浪驚起了無數飛鳥和昆蟲,云煙彌漫,長虹升騰而起。紺碧的浪濤洶涌拍岸,如被巨龍挾卷著奔涌到青眼前。7K妏敩
他足尖在畫舫頂上輕輕一點,姿翩若驚鴻,迎著十余丈高的浪頭高高躍起。寬大的青袍袖中,雙手結龐大的水印,正正印在水霧青空之上。
水印仿佛在空中破了一扇紙窗,瞬間將浪濤化作一條水龍,直吸窗口而去。水龍被水印控制了頭顱,軀還在力掙扎,掀起層層碧浪。
青人手印合,指尖在口一,再度向外力推,水龍掙扎片刻,終于長嘯一聲,仿佛被馴服一般,再度集聚流,匯了水印中。
Advertisement
水龍上天,先是龍頭,跟著是龍,最后是龍尾。最后一水流砰然撞擊在水印上,水印已轟然收攏,水流被擊碎無邊的漫漫煙雨,降落在江畔眾人的臉頰之上,溫宛如桃花瓣落。
眾人驚愕無言,紛紛被煙雨迷了雙眼,再睜開眼時,江中的青人和桃花汛都已不見了。
江面平如鏡,只有一道長虹橫江而臥,提醒著眾人并非夢境。
不知過了多久,終于有人高起來:
“那人……把桃花汛走了!”
談東樵以水印引著汴陵江水,挾云霧風雷之勢,直向西郊的方家巷子而去。
斷妄司已將方家巷子團團圍住,在上空架起無相法網,但凡人的雙眼什麼也看不到。
方家巷子里的野貓、野狗驀地狂躁起來。東家的孩子又被酒后的老爹揍得嘰哇,西家的婆母坐在門檻上聲嘶力竭地數落兒媳的錯,南家爛賭的丈夫正從媳婦手里掰搶家里最后一串銀錢,北家兩戶鄰人正在為隔墻上一株野桃樹的歸屬打得頭破流。
久居此地的人們對紛的世界習以為常,并不關心突如其來的巨響。
只有一個出門撒尿的小,在院子里解開衩的時候,偶然抬頭看了看天。
“娘,天上有水龍過來啦!”
小招引了母親,母親召喚了鄰人,一傳十,十傳百,整個方家巷子的人都跑到了天的地方,仰斷脖子,瞪著這死鬼老天。
一條如龍般清冽的巨大水流從虛空中被釋放,在明的日下打了幾個轉,驀地加速向方家巷子最核心奔沖而來。水龍張開瑩瑩巨口,傾襲人間,如搏一只毫無還手之力的兔子。
天降災殃,于窮人更是雪上加霜。
求生的搶占了一切,父親抱起剛揍過的孩子,兒媳攙起還在數落自己的婆母,一無所有的丈夫將雙臂護在妻子頭上,鄰人手拉著手,過矮墻。人們痛苦慘,但依然扶老攜,以人類能夠達到的最快速度,向生路奔逃。
出乎凡人們的意料,龐大水龍并未摧枯拉朽般沖垮殘舊的房屋,卻在半空被截住了。水流仿佛撞在明的網之上,頃刻間被撞碎細的春雨。
春雨織煙網,雨珠細得如同豆蔻的輕吻,沾在每一個人的臉上,上,沾在孩的笑上,沁了每一寸方家巷子的土地。
天下弱者莫如水,然上善若水。這是一場最不同凡響的桃花汛,汴陵的江水以方家巷子為口,倒灌沉積固化了多年的聚金法陣,一節一節沖開沉疴。
而沉迷在百代富貴幻夢中的高門大戶,還未覺察。
吳王府,地下祭堂中,春花按了按鐲子,對面聲音已歸于無聲。知道,談東樵已依約而行。
春花轉向霍善與吳王:“上面那位神尊,其實只是個凡人,名錢仁。他以怨報德,吞食了鼠仙子恕的妖力,將子恕所建的聚金法陣收為私用。如今的尋家、梁家,都是錢仁的后人,他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圓自己一族長命富貴罷了!王爺、道尊,你們都是久歷世事的人,吃過的鹽比小子吃過的米多。滿口萬民福祉,實則中飽私囊之人,你們見得還麼?”
這話一出,霍善神只微微一,吳王卻是心神大,地回過頭,向神像。
神像察覺了他的疑慮:“王爺是在質疑本尊?”
吳王忙低下頭,連稱不敢。
神像冷冷哼了一聲:“你且看看,是誰回來了?”
春花轉過,一甜膩的暖香撲面而來,悉得令人心悸。
俊的青年素白靴,右手持劍,左手持鞘,踏寒而至。他蒼白,仿佛比從前最病弱的時候還要清瘦幾分,眉目中不見了慣常的矜暖,也不是帶著阿九記憶時的倉皇迷,而是純然的冷漠。
耳側垂下的鬢發,有一綹格外短。
“長思哥哥?”春花頓了頓,又喚了一聲:“阿九?”
神像——即是錢仁桀桀而笑:
“此刻他心全由本尊差遣,哪里還聽得見你的聲音?”
春花聲音有些抖:“你……對他用了裂魂香?”
裂魂香,腠理,割發裂魂,善惡各行。
藺長思腳下未停,手中長劍向前,直指著。他的左肩上,半個魂魄孤苦無依地凝著。
吳王直起子,錯愕道:“神尊,您不是要以長孫春花的醫治我兒麼?為何……長思會變這個樣子?”
猜你喜歡
-
連載2398 章

蠱真人
人是萬物之靈,蠱是天地真精。 三觀不正,梟魔重生。 昔日舊夢,同名新作。 一個穿越者不斷重生的故事。
641.7萬字8 15165 -
完結3041 章

太古武神
少年葉楓,心誌堅定,因天賦太差,遭未婚妻拋棄。、當偶獲不滅金身決,從此開啟一條不死不滅的殺伐之路。這個世界,強者為尊,葉楓要成為強者中的強者,鑄就一代太古武神
540.6萬字8.18 491238 -
完結632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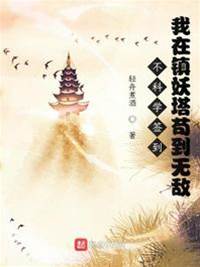
不科學簽到:我在鎮妖塔茍到無敵
藍星進入超凡時代,萬物進化,妖獸橫行。人類在進化中覺醒星魂,從而對抗肆虐的妖獸。在鎮妖塔打雜的周玄意外覺醒不科學簽到系統。在太古荒獸身上簽到,獲得洪荒之力。在雜草精身上簽到,星魂進化為九葉劍草。千年玄龜、萬年海王,不死真凰、吞天神龍,都成了他簽到的對象。鎮妖塔內妖獸無數,周玄默默簽到,一不小心就無敵了。
124.2萬字8 20336 -
完結663 章

驚世靈師:廢材五小姐
古武世家的繼承人楚玲,被愛人設計滅族,死後穿越到了幻靈大陸。 天生廢材?傻子小姐?哼! 那些都已經成為了過去,未來她將是這世界上最高存在的靈師。 話說,這位天神,雖然你一直護航,伴我成長,可大白天你壓著我,還扯我衣服幹嘛?某天神左手一扣,右腿一勾,逮住想要逃的某女,嘴角揚起邪魅的弧度:當然是造小鳳凰了。 Tags:驚世靈師:廢材五小姐、二月、驚世靈師:廢材五小姐txt全集下載、驚世靈師:廢材五小姐無彈窗、驚世靈師:廢材五小姐最新章節、驚世靈師:廢材五小姐txt全文下載、驚世靈師:廢材五小姐全文閱讀
119.8萬字8.18 15771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