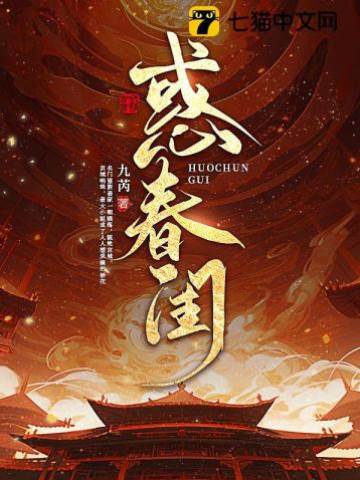《替身竟是本王自己(雙替身)》 第 47 章 四十七
桓煊目一凝,隨即面焦急之,問那中道:“傷在何?”
中道:“傷在后背上。”
桓煊對醫道:“鄭奉去院吧。”
鄭奉道:“殿下的傷……飛霜殿還有兩名侍醫,老夫人請他們來給殿下醫治……”
桓煊道無礙,看了眼給他打下手的年輕醫:“這位司醫留下便是。”
又對那中道;“你們先去院,孤稍后便到。”
太子傷,他這個胞弟但凡沒有下不來床,總是要去個臉的。
醫替他檢查左脅的傷口,他傷得不算重,但因為一直在奔走,傷口幾度崩裂,又沒及時敷藥,傷口便有些紅腫。
醫替他清洗了傷口,敷上傷藥,重新包扎,末了叮囑道:“殿下這幾日請小心靜養,以利愈合。”
桓煊命侍賞了他財帛,將他送出殿外。
醫走后,桓煊簡單拭了一下,換了裳,在隨隨床邊坐下。
背上有傷,只能側躺著,顯然睡得不穩,雙眉蹙,睫不時輕輕,額頭上不斷有冷汗沁出來。
桓煊人換了熱水來,絞帕子替拭額頭上的汗,將鬢發掠到耳后,用手指眉頭,可剛展平,立即又皺了起來。
高邁在一旁等了半晌,終于走上前來,言又止道:“殿下,院那邊……”
桓煊頷首:“孤知道。”
他握了握隨隨的手:“我要離開片刻。”
隨隨在睡夢中回握了他一下,喃喃地喚了一聲“殿下”。
桓煊心尖一:“很快就回來陪你。”
到得院,皇帝、大公主和一干皇子都在。
皇帝見了他道:“三郎也傷了,傷勢如何?”
桓煊道:“只是些許皮傷,已無大礙。二哥傷勢如何?”
Advertisement
皇帝朝琉璃屏風了眼:“沒有命之危,鄭奉正替他上藥,我們進去看看。”
桓煊隨父親繞過屏風走到榻前,只見太子趴在榻上,鄭奉正替他清理傷口,阮月微坐在榻前握著太子的手,見到桓煊,不自覺地松開夫君的手,隨即才回過神來,起向皇帝斂衽行禮,又對桓煊道:“三弟來了……”
桓煊微一頷首:“二哥怎麼樣?”
阮月微哽咽道:“殿下為尋我遭賊人伏擊,賊人砍傷后背,失了許多……”
桓煊看了看太子背上的傷口。
他的傷勢比預料中更嚴重,一條斜斜的刀傷橫過后背,深幾乎見骨,中后背已被全浸了。
他故意傷以避嫌疑,也算是下了本。
桓煊向他行禮:“二哥,弟弟來遲了。”
太子緩緩睜開眼睛,氣若游道:“是三郎來了……”
沖他勾了勾角:“你也有傷,不躺著靜養,來這里做什麼?”
桓煊道:“只是些許小傷,二哥了這麼重的傷,理當來探。二哥眼下怎麼樣?”
太子道:“皮傷罷了,不值得大驚小怪。”
頓了頓,目了:“多謝你把阿阮平安帶回來,只是連累你也了傷……”
他這麼一說,那些死士的目標便了他自己,而桓煊只是因為越俎代庖去救太子妃,這才落埋伏牽連畢竟阮月微是太子妃,用作餌理所當然是為了謀害太子,誰也說不出個不是。
可即便猜到他心思,桓煊也不可能對阮月微坐視不理,太子便是算準了這一點。
桓煊道:“二哥不必見外,這是弟弟分所應當之事。”
頓了頓道:“二哥是在哪里遇伏的?”
太子道:“在行宮西北三十多里,出了圍場地界……”
Advertisement
“刺客有多人?”桓煊問道。
“黑夜里看不清,總有好幾十人吧……”太子想了想道,“我帶去百來個隨從和羽林衛,折了一大半在那里。待天明侍衛去清點尸。”
頓了頓道:“幸而捉到兩個活口。”
桓煊目微:“可問出刺客來歷?”
太子道:“已將人給沈將軍去審問了。”
右千牛衛大將軍沈南山是皇帝親信,太子既然敢把人給他去審,自然是準備了萬全之策。
話音甫落,便有侍在屏風外稟道:“啟稟陛下,沈將軍求見。”
皇帝道:“請他在殿外稍待片刻。”
等鄭奉幫太子包扎完傷口,皇帝這才屏退了醫、侍和宮人,又和悅地向阮月微道;“阿阮也累了,先去殿歇息吧。”
阮月微知道這是要支開自己,便即斂衽一禮,退至殿。
桓煊也行禮道:“兒子告退。”
皇帝看了一眼太子道:“三郎不是外人,留在這里一起商議。”
桓煊道是。
皇帝便向中道:“請沈將軍進來。”
沈南山走進殿中,行過禮,對皇帝道:“啟稟陛下,那兩個刺客已經招供了。”
皇帝道:“是了何人指使?”
沈南山道:“他們招認是淮西節度使指使,來刺殺太子殿下。”
此言一出,連桓煊都有些訝異,他以為太子可能會順勢賊喊捉賊,他卻比他料想的更老謀深算,將皇帝的心思得一清二楚。
淮西藩鎮雖然只有三州之地,卻地大雍的腹心,扼南北漕運之咽,如今的節度使郭仲宣貪得無厭,朝廷每年都要花費大量稅錢安,是皇帝一直以來的心腹大患,比河朔更危險。
皇帝一直有征淮西的念頭,只是朝臣中有不反對的聲音,遂舉棋不定至今。將行刺一事推到淮西節度使上,無異于給皇帝遞了刀柄。
Advertisement
而眾所周知太子是主戰的一派,淮西節度使想要除掉他也說得過去。
即便皇帝心知肚明其中有太子的手筆,也會趁此機會堵上朝臣的,發兵征討郭仲宣。
且皇帝讓太子與三子互相制衡,若是廢除太子,齊王順利章立為太子,到時候即便卸了他的兵權,他在神翼軍中的威信卻是一時半會兒不能消除的,對皇帝來說難免是種威脅。何況朝廷缺將才,征討淮西他是最適合的將領。
桓煊不由對這二兄刮目相看,若是栽贓嫁禍給他,皇帝不可能相信,定要命人追查,再周的部署也經不起細查,而他這一招禍水東引,卻正合皇帝的心意。
卻是他低估了太子。
果然,皇帝然作:“郭賊好大膽子,竟敢謀害儲君,傷我二子,是朕這些年對淮西太過姑息了。”
他走到太子榻前,俯溫言道:“二郎放心,阿耶定然給你個代。”
又對桓煊道:“三郎這段時日便留在行宮中將養,此離兵營也近,待你養好傷便加練兵,早日替朕將那郭賊碎尸萬段!”
桓煊知道父親對淮西志在必得,他雖不主張用兵,但也只能道:“兒子遵命。”
皇帝拍了拍他的肩膀:“回去歇息吧。”
桓煊向父兄行罷禮,出了太子的寢殿,正要登輦,忽聽有人:“三郎留步。”
他轉頭一看,卻是長姊提著子追出來。
桓煊道:“阿姊何事?”
大公主歉然道:“聽說我府上的侍衛里混了細作,傷了你那個……都怪我選人的時候心大意……”
那侍衛容貌出眾,世也清白,是以府雖只有半年,在挑人隨行時一眼便挑中了他。
桓煊雖不至于遷怒,也沒什麼好臉:“阿姊往后謹慎些便是。”
Advertisement
說著便要上步輦。
大公主拉住他道:“那小娘子傷得重麼?”
桓煊臉一沉:“托長姊之福,萬幸沒死。”
大公主吃了一驚,這三弟子冷,自小與不親近,但在面前一向都是客氣疏離的,這還是第一次見他發脾氣,可見他待這侍妾很不一般。
可這麼喜歡,為什麼不給個正經名分接進府里呢?雖說娶妃前府里有個貴妾說出去不好聽,可養著外宅也不是什麼好名聲。
想了想道:“害傷我也過意不去,總得想個法子補償才能心安。跟著你,財帛肯定是不缺的,你替我想想……”
桓煊正想說不必,忽有一個念頭閃過,改口道:“阿姊有心,既如此,弟弟便不同你見外了。”
他的態度一下子拐了個大彎:“不如就勞煩阿姊向阿耶陳,替請一個封號吧。”
大公主吃驚地張了張,這小子還真是不同見外:“這……”
桓煊道:“若非不顧替我擋了一箭,眼下命垂危的就是我了。我這條命,怎麼說也值個鄉君封號吧?”
頓了頓,冷了臉:“阿姊若覺為難便罷了。”
大公主一想,如果沒有這子擋下這一箭,傷的便是桓煊,若再有個好歹,便是的疏忽害死了自己親弟弟。
且不說父母會怎麼追究,這輩子怕是都不能心安了。
這麼一想,鹿氏簡直是的恩人。
忙道:“不為難不為難,一個鄉君罷了,我去同阿耶說,你放心。”
桓煊這才緩頰,向一揖:“那便多謝阿姊了。”
大公主雖有些枝大葉,人卻不傻,知道他替那子請封,自然不只是為了給一個出。
那子出雖貧苦,至是良籍,進王府做個孺人已夠了。他替討封號,這是要納作側妃?
這倒是令始料未及。
他尚未娶妃,府里有一兩個貴妾沒什麼大礙,可側妃先于王妃進門可就是大事了。
這些事本該由母親過問的,奈何皇后對三子不聞不問,連婚事都不管,只能這做長姊的多心了。
大公主言又止道:“三郎,這鹿娘子替你擋箭,你看重些無可厚非,但恩寵太過于未必是好事……”
桓煊頷首:“我知道。”卻是一副油鹽不進的模樣。
大公主暗暗嘆了口氣:“阿姊就不和你拐彎抹角了,阿耶替你相中了阮家六娘子,你究竟意下如何?”
桓煊一聽提起這事便不自覺地皺了皺眉:“上汜那日我便同阿耶說過無意娶妃,遑論阮氏。”
大公主一時也有些鬧不明白了,他因為放不下阮月微才找了個肖似的替,那阮六娘分明是堂姊的翻版,他卻偏偏不要。
“可你總是要娶王妃的,到時候新婦進門,你鹿氏怎麼自?”
“不娶就是了。”桓煊毫不猶豫道。
大公主一噎:“你……難道就一輩子守著個妾室過了?”
桓煊敷衍道:“以后的事以后再說,有勞阿姊先替請封吧。”
“我省得,”大公主道,“可你婚事總是拖著,阿耶那邊也代不過去。”
桓煊道:“阿姊放心,這一年半載阿耶不會催我。”
大公主詫異道:“出了什麼事?”
皇帝信賴長,朝政之事也常上一起討論,桓煊也不瞞,直言道:“阿耶打算對淮西用兵,不出意外是我領兵。沒幾日就該定下來了。”
至多四五個月,待糧草調集,他便要出征淮西,皇帝自然不會在這種時候催他娶妃。若能打下淮西,將三州重新納朝廷治下,到時候他提什麼要求父親都不好拒絕,娶平民子為妃雖然驚世駭俗,但他執掌重兵,皇帝私心里并不希他娶個高門世家的子為妃,到時候他多求幾次,父親多半就半推半就地允了。
桓煊自然不會把這些打算告訴長姊。
大公主就是做夢也想不到他打的是這主意,只是詫異道:“怎麼突然就要發兵……”
知道朝廷上下為了淮西問題爭了兩三年,一直沒吵出個結果,家駙馬便是史,為此不知打了多仗了。
突然就決定下來,必定有什麼緣故。
立即想到今晚之事:“莫非……”
桓煊點點頭。
“難怪……”大公主著下頜若有所思。
桓煊道:“弟弟先告辭了,阿姊別忘了請封的事。”
猜你喜歡
-
完結906 章
攝政王是病嬌,要寵著
【重生+甜寵+虐渣+爽文,男女主1v1】身為丞相府千金嫡女的南曦,上輩子腦子被門夾了,喜歡上那個徒有其表卻滿肚子陰毒詭計的渣男,落了個眾叛親離淒慘死於渣男賤女之手的下場。重活一世,她智商上線,看著身邊這個權勢滔天,容顏俊美的攝政王,忍不住再次懷疑自己的眼光,攝政王殿下要顏有顏,要權有權,還對她千依百順,她怎麼就眼瞎放著珍珠選了魚目?隻是這位攝政王殿下時不時地心疾發作,是要鬨哪樣?攝政王是病嬌,要寵著
147.7萬字8 33340 -
完結17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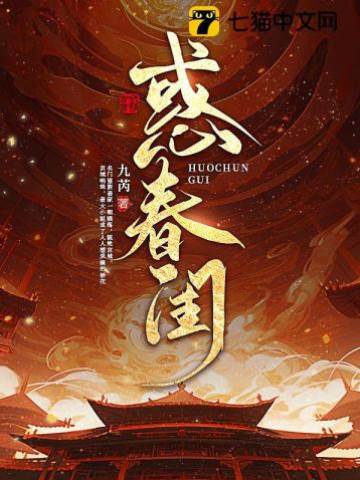
惑春閨
名門望族薑家一朝隕落,貌絕京城,京城明珠,薑大小姐成了人人想采摘的嬌花。麵對四麵楚歌,豺狼虎豹,薑梨滿果斷爬上了昔日未婚夫的馬車。退親的時候沒有想過,他會成為主宰的上位者,她卻淪為了掌中雀。以為他冷心無情是天生,直到看到他可以無條件對別人溫柔寵溺,薑梨滿才明白,他有溫情,隻是不再給她。既然再回去,那何必強求?薑梨滿心灰意冷打算離開,樓棄卻慌了……
31.5萬字8.18 7894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